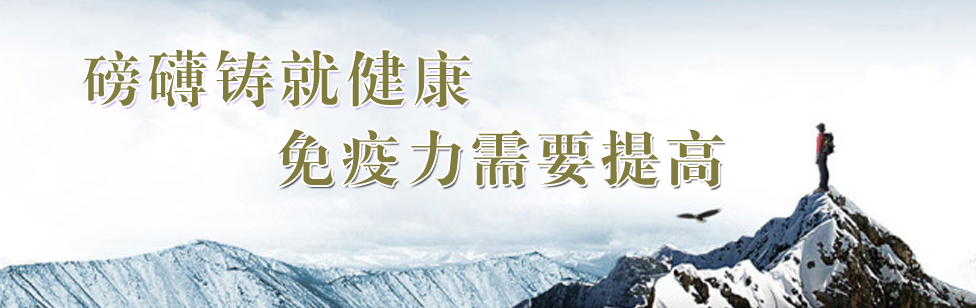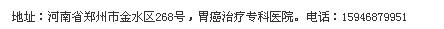大型传奇围棋小说《乌鹭传》
来源:国学网
年,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
在时代剧变的同时,中国围棋也正进行着除旧布新的变革。清末、民初间,正值中国围棋的传统“旧法”(置有“座子”的旧式棋法)与“新法”(废除“座子”的现代棋法)交替的时期。随着中日棋手之间的接触交流,在棋界掀起了一股学习日本棋艺的新风。在提高棋艺方面,生活在这一特定时期的中国棋手不仅有与日本棋家交流的机会,又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日本棋谱可资借鉴,比单纯效法古谱的清末棋手肯定有利得多。所以,民国期间中国围棋水平比清末有所提高,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出于复杂的社会原因,民国围棋进步的速度仍相当缓慢。
辛亥革命后,中国资本主义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此时中国人民并未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国家也没有获得真正的统一。在前后近40年的民国时期,内战、外战、大小军阀混战蜂起。这样多变、多难的时局势必严重影响包括围棋在内的各种文化、艺术的发展。因此,尽管民国棋手已接触到比较先进的棋理,又对围棋振兴怀有强烈的愿望,然而,处在这样特定的时代环境中,他们的才智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旧中国政府也从未为提高围棋水平创造必要的条件。以下展示的民国棋界状况,正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经济收入方面,民国棋手主要靠“赌彩”、“帮彩”与传授棋艺。这种相沿已久的旧生活“模式”虽然也促使他们比以上层文人为主体的清末棋手重视棋艺进修,但此时民贫国匮,单纯以艺谋生,将显得十分艰难。所以多数棋手仍要兼有它职,才能维持温饱,一旦时局变化,他们还要为衣食走南串北。由于生活得不到保障,决定了棋手社会地位的低下,也严重妨碍了民国围棋的进步。
民国时期没有全国性的围棋组织,也没有由国家机构创办的棋社、棋院。重要围棋交流通常只能在供来客对局的大小茶楼(馆、室)与棋会、棋社(包括由地方棋手联合组织的棋会、棋社,私家举办的棋会,棋社)等场所进行。这类茶楼、棋会属于私家经营,基础比较薄弱,一旦遇到实际困难,就随时可能倒闭。但在漫长的旧中国时期,它门就是中国棋手切磋棋艺的基本阵地。
民国年间知名棋手主要聚集在大型城市进行交流。因为大城市不仅是文化、经济的中心,而且拥有多层次的棋艺爱好者,棋手在这里也有较大的活动余地。可是,知名棋手都走向大城市,中、小城市的棋手就难免囿于见闻,不利于地方围棋活动的开展。这一现象,直到三十年代后才稍有改观。但就全国而言,围棋普及的程度仍十分低下。
民国时期从未举办全国性围棋竞赛,以致不同地区的棋手很少有互相交流的机会。到了三十年代中期,由于地方围棋组织不断增多,围棋活动比较频繁,开始进行跨越地区的城市之间的围棋比赛,并有进一步向全国性围棋竞赛发展的趋势。旋因年抗战全面爆发,各地棋友星散,组织大型比赛自然更无希望。
民国时期出版的围棋书谱与有关著作种类繁多,大致分编译日本棋谱、介绍中日交流对局、翻印古谱,以及围棋笔记、棋话等,涉及面相当广泛。另外,由于民国时期报刊盛行,为宣传围棋提供了方便;少数围棋组织还出版围棋定期刊物,受到读者的欢迎。可是,不论报刊围棋栏或是定期围棋刊物,都因社会动荡,无法长期坚持。
在民国时期,只要时局相对稳定,围棋活动就呈现上升的趋势。例如:二十年代前期的北京,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三十年代中期的上海、南京,抗战胜利后的上海等,都曾在短暂的安定环境中涌现许多名手和大小围棋组织,也冒出一些才能出众的青少年棋手。足见在广大群众中对开展围棋活动蕴有很高的热情,民国棋手也为推动围棋的发展作出不懈的努力。可是,在政治腐朽、民生艰难的旧中国,这样的“兴旺”终究不能长期维持。直至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国内仅有少数棋手达到专业四段的棋力,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很大的差距。
1.中日围棋交流
民国建立直至四十年代初期,来访我国的日本棋手络绎不绝,其中,除少数属于旅游性质或在中国侨居外,多数均由我国棋界支持者聘请前来。通过棋艺交流,加深了两国棋手之间的友谊,也促使中国棋艺不断提高。据现存资料作不完全统计,除高部道平从年至年间屡次来访外,还有十几位日本棋手来访。
影响较大的来华访问有:
年,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段祺瑞邀请日本名手广濑平治郎(六段)访北京,广濑的弟子岩本薰(初段)亦随同前来(见日本林裕《大正围棋史年表》)。翌年,广濑与岩本薰又同访上海,当时上海名手张澹如、潘朗东、吴祥麟等与广濑对局被让3子,与岩本对局被让先二,可见此时我国围棋水平仍然低下。
年5月,日本濑越宪作(五段)来青岛漫游,因由驻华日本某军官的介绍,濑越前往北京,受到段祺瑞的接待。濑越在京与中国棋手汪云峰、伊耀卿、顾水如等屡次对局,濑越归国后,发表《支那之棋界》,对近代中、日围棋交流经过,中国棋界支持者与知名棋手,中日围棋规则的差异均有阐述。此后,濑越长期留意中国棋界动态,接连发表了《中国棋界之现状》、《西车南船游记》、《访问中国》等多篇文字,热情宣传中国围棋的进步。
年秋,段祺瑞与当时财政总长王克敏集资聘请日本名人本因坊秀哉来访。秀哉到北京后,除与濑越宪作下了半局表演棋外;其余均下让子棋。随后秀哉又应南方名手的邀请,来到上海。这是民国时期日本“名人”唯一的一次来访。从现存记录来看,当时中国名手善耆、顾水如、潘朗东、何星叔及段祺瑞等均被秀哉让3~4子。据日本《名人·本因坊秀哉》记载,秀哉于9月27日离日本来访,11月24日归国。
年夏,日本加藤信(五段)来访上海,南方名手范楚卿、潘朗东、方金题、何星叔、吴祥麟、唐善初、王子晏、刘俨廷、宋怀仁等先后受到他的指点。
年春,日本铃木为次郎(六段)经新加坡来到上海,在张澹如宅居住一月有余与上海棋手张澹如、何星叔、潘朗东、吴祥麟、王子晏、陶审安等广泛交流。上海名手陶审安奉铃木为师,经常向他请益。铃木归国后,仍与陶继续书信往来,双方曾就古代“围棋十诀”的内容进行反复研讨,并试行文字上修饰与订正(见《东瀛围棋精华》、《围棋》)。
二十年代初、中期,日本棋手赤岩嘉平(三段)、安藤馨(三段)、山平寿(四段)、都谷森逸郎(五段)等先后在上海交流。此间,中国王子晏棋力剧增,他与日本棋手对局中获得很高胜率(见胡沛泉《围棋纪录·故王子晏对局自留棋稿总统计》)。
年8月,日本岩本薰(六段)、小杉丁(三段)来访。8月20日,岩本薰在北京富户李律阁宅与年仅12岁的中国少年吴泉(清源)对局。吴在初让3子的条件下战胜了岩本,改让2子后,吴少年始以微差致败。3天后,岩本薰又在李律阁宅让汪云峰及刘棣怀2子对局,岩本战胜了汪云峰,但负于刘棣怀。顾水如、王子晏、刘棣怀、吴清源等棋手的涌现,证明中国棋界已逐渐换上了一代新人,岩本薰归国后,发表《支那漫游记》一文,记述了与中国棋手切磋的实况。
年冬,日本井上孝平(五段)前来北京与此时已有“神童”之誉的吴清源对局,初由井上让吴清源2子,连弈2局,井上均因形势被动打挂。于是井上主动提出将棋分改为让先。继而再弈3局,双方1胜、l负、1打挂。井上局后,对吴清源的棋才惊叹不止,发表感想说:“他(吴)已知道日本人所弈的棋形,而且隐约看出他有改进日本棋形的迹象。”这无疑是对吴少年棋艺才华的高度评价。由于岩本薰、井上孝平等日本棋家归国后广泛宣传,吴清源的才能终于引起中、日棋家的 年9月,日本濑越宪作派遣他的弟子桥本宇太郎(四段)前来北京,进一步考察吴清源的棋力,结果吴清源执黑2局连胜。同年lO月,在中外友人的协助下,吴清源东迁日本深造,后来终于成长为名满天下的大国手。
年7月,日本濑越宪作(七段)、桥本宇太郎(四段)来访上海,与上海棋手张澹如、吴祥麟、潘朗东、王子晏等切磋棋艺。此间,王子晏执黑对桥本的一局棋弈了3天,费时15小时以上,始以和局告终(见濑越宪作《西车南船游记》)。
年7月至8月,日本筱原正美(四段)、小杉丁(四段)来访上海。上海上场棋手有王子晏、潘朗东、刘棣怀、魏海鸿、陈藻藩、张澹如等,阵容相当雄厚。对局虽然均由中国棋手执黑先行,但日双方竞争激烈,胜负之数往往在毫厘之间,而屡次出现一局棋连弈两三日的现象,可见中国一流棋手已对日本四段棋手构成威胁(见日本小杉丁、筱原正美《中华棋坛访问记》)。
年5月至7月,日本木谷实(六段)、吴清源(五段)、安永一(日本棋院编集总长、当时四段)、田冈敬一(当时初段)来访上海、无锡等地。此时木谷与吴清源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由他们共同创造的“新布局”风靡一时,对中国棋界也有巨大影响。我国名手顾水如、刘棣怀、魏海鸿、王幼宸、雷溥华、张澹如、张恒甫、沈君迁等先后登场。其中刘棣怀、顾水如曾执黑战胜安永一,魏海鸿在被让2子时曾胜木谷实,但在被木谷、吴让先的对局中全部败北。这一战绩,证明当时中国棋手尚不具备冲击日本一流棋家的实力。
年10月,日本濑越宪作(八段)、吴清源(八段)、桥本宇太郎(七段)、井上一郎(四段)一行来访,曾与上海、南京及北方南下棋手交流。此间正值抗战时期,民族矛盾尖锐,但懒越一行访问期间曾向部分中国棋手赠送“段位”,对中国棋界产生了影响(见桥本宇太郎《日华手谈》)。
民国时期,原先一直在低谷徘徊的中国围棋终于摆脱了传统着法的束缚,提高了艺术境界,这与日本棋手的来访、指导,以及日本先进围棋技术的引进,有着紧密的联系。当然,由于民国时期国情复杂,少数日本战争罪犯曾违背人民意志,悍然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极其严重地破坏了包括棋手在内的两国人民之间的正常交往。尤其是年至年间,这是中、日交流史上“只留下流血和破坏的最坏的八年”(引自日本滕加礼之助《中日交流二千年》)。此间,沦陷地区虽然也曾出现以伪政权名义建立的棋院,如年在伪“满洲国”新京(长春)成立的“满洲棋院”,年伪“华北临时政府”在北京成立“华北棋道院”,以及在青岛、鞍山、汉口、开封等地先后设立的“支部”或“俱乐部”,实际上这都是些受日伪操纵的围棋组织(见日本年版《大手合精选·棋界一年》、日本林裕《围棋百科辞典》等),其目的也不在于宣扬棋道。但从长达两千年的中日交往史来看,唯有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才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而围棋在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与沟通情感方面,无疑起有积极的作用。围棋由中国传向日本,反过来中国棋手又向日本棋手学到很多有益的棋理与知识,这对中国围棋的发展与围棋走向世界,都具有深远意义。
2.棋界的“南北护法”
民国时期政治中枢腐败无能,内战频仍,国家无力倡导和支持围棋事业。因此私人赞助围棋曾起到不小的作用。当时有两个人,或有权势,或有钱财,在自己家中招揽天下棋客,积极促进中日围棋交流,对于维持华夏神州的棋运,作出较大贡献。这两个人即是北京的段祺瑞和上海的张澹如,当年被棋界人士誉为“南北两大护法”。
段祺瑞(-),安徽合肥人。继袁世凯之后掌握北洋军阀政府大权、号称“北洋之虎”。段祺瑞虽有这个浑号,但若以为他是粗犷彪悍的绿林汉子。那就错了。实际上他是一个文静深沉、能诗能文的人。段祺瑞酷嗜围棋,也喜欢敞开家门招待南北棋客。因此在他权势显赫,炙手可热的时期,他的府邸(北京东绒象鼻子后坑),过往围棋高手川流不息,颇有“一登龙门声价十倍”之感。凡段氏门下常客,每月咸有津贴,足以维持一般生计。
关于段祺瑞的棋力,诸方说法不一。不过在当时却有“殿样棋”的称号,所谓“殿样”乃是流行日本棋界的一种调侃语,含有唯我独尊之意。他有个习惯,每逢星期日六点左右便步出内室,与府邸的棋手下棋,或观看棋手之间的对局,然后请大家共进早餐。他行棋时落子如飞,直感力很强,同时他的自尊心也比常人强出几倍,输棋便恼。这一点棋客们尽人皆知。俗话说:“伴君如伴虎”,他门下的棋客原来都忌些颇负时誉的高手,但为了不扫他的兴致,常常卖个破绽,故意败下阵来。老段亦沾沾自喜。据说他下棋往往采用一种模式:布局时相互围空,中盘时双方围空基本完成,老段便猛然打入对方空内,只求活一小块便罢。老段称之为“花园里面建小舍”。每逢此时,对方总是左右为难,既不敢将打入的棋子吃掉,又不敢在段总理的宝地上动士,因而老段便成了常胜将军。
少年吴清源经名手顾水如介绍,也成为段门座上客,并且每月以学费为名领取元的补贴。他曾与段总理下过一局棋,老段仍旧象平时那样蛮横无理、盛气凌人,满不在乎地走出无理着法。吴清源毕竟是个孩子,童心未泯,也就毫不客气地拼命追杀,结果将段总理的棋大部分吃掉。当时在场观战的棋手和随从们都捏着一把汗,最后老段无奈,只好投棋认输,拂袖而去,一整天再没露面。可怜那天大家连照例的早饭都没混上,只好饿着肚子回家。吴清源也被顾水如训斥了一通。从那以后,段祺瑞再也不找吴清源下棋了。尽管如此,每到月底,吴清源去求取百元的补贴时,老段依旧照数发给。
段祺瑞下棋时的唯一克星是他的儿子段宏业,此人棋术高强,能与座上的一流好手一争短长。当父子两人下棋时,儿子明知父亲好胜,偏不买账,下手毫不留情杀个痛快,往往惹得老段勃然大怒。据说有一次段宏业在外地,老段突然通知说要见他,儿子不知发生了什么急事,匆忙乘火车长途跋涉赶回北京。谁知老段二话没说,先和他下一盘棋,结果儿子又胜老子。老段推枰而起,骂小段说:“你小子除了下棋没别的能耐,马上给我滚回去!”
当年出入段公馆的国内高手,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张乐山,汪耘丰、顾水如、吴清源外,还有刘棣怀、雷溥申、雷博华、金亚贤、崔云趾、王幼宸等人。这些人都是职业棋手,但也大多以担当秘书或嘱托为名受骋,出入权贵者的府邸。这样在北京的段公馆内,也就形成了一个全国围棋活动的中心。
段祺瑞不仅在自己手下聚集了不少国内的围棋精英,还时常聘请日本高手来华,进行棋艺指导。年秋,段祺瑞邀请日本广濑平治郎六段来访,同来的广濑的弟子岩本薰初段是个未满17岁的少年,他同老段对弈时也有失“恭敬”,事后被广濑训斥了半天。年5月,日本濑越宪作五段来我国青岛施游,历时约两个月,夏秋之交前往北京,受到段祺瑞的欢迎接待。彼时濑越年富力强,技艺高超,让子棋尤为出色。名手如汪耘丰、伊耀卿等均被让至三子,顾水如因熟悉日本布局,独能受二三子对局。与此同时,段祺瑞又邀请日本“本因坊”秀哉来北京,成为当时轰动的事件。其间也发生了一些有趣的纠纷,当段祺瑞与秀哉对弈时,老段仍要拿白棋,秀哉不肯,坚持必须让子。争到最后,老段虽然同意让子,却死抱着白棋不放,结果就在棋盘上摆上两枚白子。对局前,也有人劝秀哉手下留情,秀哉不答应,说“回去不好交待”。结果秀哉连胜三局。同年11月,秀哉准备启程回国,向北洋政府讨取原先说好的盘缠,老段给他来个闭门不见。秀哉无奈,只好托人说合,约老段再战一盘,故意输棋,换得元路费。
年3月18日,段祺瑞命令卫队向北京反帝爱国的示威群众开枪,伤亡百余人,一手制造了举国震惊的“三·一八”惨案。4月,他终于被国民军赶下台,黯然退居天津寓所,结束了军阀的政治生涯。段门的棋士们失去了庇护和接济的靠山,只好各奔东西自谋生路。刘棣怀飘零四方、雷溥华闭门养病,金亚贤颐和园售票、崔云趾开起茶馆,号称天下第一棋士的顾水如后来也回到上海。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急欲在华北物色汉奸傀儡,段祺瑞因有亲日的背景,自然成为侵略者笼络的对象。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定迎他南下,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段祺瑞移居上海,总算成全了民族大节。年,段褀瑞在上海又一次广召天下棋客,短短数月,段公馆内又形成新的围棋中心,那些老的段门棋客重新聚集到段祺瑞身边。老段此时虽然只是寓公,但他广有钱财,依旧每月给棋客发津贴。棋客们对他也是敬畏如昔,顾水如有一次请老段授他二子,决战三局赌彩,结果竟以一胜二负败北。汪耘丰从北京跑到上海,请老段授他三子,竟一胜一负。老段喜出望外,顺手掷下0元谢礼。就在这一年,旅居日本的吴清源回国游访,在上海见到段祺瑞。老段知道吴清源在日本声誉日隆,并要加入日本国籍,不禁深为动容。不久他去庐山养病,见到蒋介石,向之建议提倡围棋,召回吴清源,否则中国的围棋将愈发一蹶不振。蒋介石哪有这种雅性,只是口头敷衍几句,过后也就不了了之。
段祺瑞一生的所作所为,大都可以否定。唯独倡导围棋、支持中日围棋交流,作出有益的贡献。对此,陈毅副总理曾说:段祺瑞之为人不足取,但有一点可取,就是爱好下棋和提倡下棋。对段祺瑞在围棋方面的贡献,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张澹如,名鉴,浙江吴兴南潯镇人。其上代以经营丝、盐起家,为南浔刘、张、庞、顾四大巨富之一,在江、浙、沪及香港、欧美均有产业。但澹如能成为民国时期棋界护法,不仅仅因为他财力雄厚,而且他还有一些政治背景。他的哥哥张静江,早年曾以巨款资助孙中山先生从事推翻满清的活动。辛亥革命胜利后,张静江以“党国元老”的资格,一度出任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后改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静江从小跛足,不良于行,人称“张跷子”。在日本尝从长滨彦八四段学棋,后与高部道平受四子。他有时在上海的寓所举行棋会,招待中日棋客。由于两腿瘫痪,不能起立,在室内坐轮椅而行,周旋于棋客之间。
张澹如则比乃兄更热衷于围棋,他的棋力不弱,落子迅捷不加思索,高部道平初来时让他三子,后减至二子。澹如于国内棋界交游极广,每日在上海威海卫路自建洋房内招待棋友,从下午2时起,供应丰盛晚餐,来者不拒,但亦以高手及知名人士为限。国内棋客来沪之熟稔者,常按月致送津贴,资助生活,使之能够潜心研究棋艺。例如嘉兴名手王子晏初到上海,澹如聘请为“证券交易所”会计,但只是挂名支薪,使子晏成为从事棋艺的“专业”棋手。对于那些生活没有着落的高手,可谓功德无量。澹如还创办围棋组织,邀集新老棋手会弈,并设对局彩金,胜负略有差别,由账房逐日登记按月分发。使棋客既有一定收益,又有高手指导,技艺水平得以迅速提高。
不仅如此,澹如还有意识地广收日本棋谱,提倡中国棋手研究日本新法。他经常邀请和接待日本高手来访,支付旅费和对局酬金,促进中日围棋交流。例如年7月瀨越宪作,桥本宇太郎访问上海,年4月小杉丁、篠原正美访问上海,都由张澹如在家室接待,并安排与中国棋手对局。
出入张门的“职业”高手,除王子晏外,还有魏海鸿,潘朗东、吴祥麟、陈藻藩等人。由于澹如的鼎力支持,在二三十年代,对上海围棋的发展,起过相当的作用。
当棋界两大“护法”声势鼎盛时期,南北知名棋客,不入段门,即入张门。实际上形成两大围棋活动中心。开始时界限分明,彼此之间也进行过激烈角逐。20年代末,王子晏高踞南方棋界首席,无能匹敌。北方棋界颇不服气,曾推派顾水如南下挑战,未能得利。年又推派刘棣怀南征,获得快胜。刘棣怀不打谱,不用常规,以扭杀见长,素有“刘大将”之称而蜚声北地。他知子晏布局定式极熟,官子尤楛,若按部就班,平稳弈去必输无疑。所以一上来就扭住厮杀,子晏素来认真,往往白日鏖战,夜间还苦思冥想,不能成眠。但他患有肺疾,体力不支,结果被刘棣怀打下擂去。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两大“护法”先后衰落,南北棋客串连日久,彼此互相影响声援,界限也逐步沟通。段祺瑞于年去世,张澹如也因体弱多病,于40年代初期杜门谢客。自此之后,国内知名棋客失去两大靠山,生活艰难,各奔东西,自谋生路,棋坛的情况愈显凋敝。
总之,民国时期,我国的围棋衰落,“振兴”二字是谈不到的,但是在二三十年代,依赖段祺瑞和张澹如的赞助支持,尚能维持一种小康的局面。在政府方面无力顾及围棋事业的情况,这种私人的贡献更有其难能可贵之处。
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