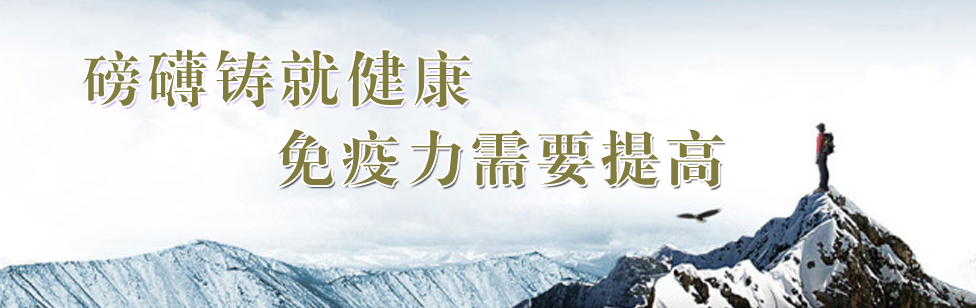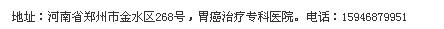病例实战巡礼:S8背侧亚段解剖性肝切除
近年来,“解剖性肝切除”的概念和临床实践在国内逐渐普及和开展。但国内许多年轻的肝胆胰外科医生对此类手术可能还比较陌生。今天这篇笔记将通过一个实际病例,介绍“解剖性肝切除”发祥地——东大肝胆胰外科是如何灵活运用和传承这一术式的。
因保护病人隐私需要,不直接引用报告原文,而报告学习体会。在不影响客观事实的前提下,文中涉及病人具体信息的部分将被隐去或模糊化处理。本手术在空间较为狭小的手术室开展,因此部分照片因拍摄角度和显示屏幕老旧的关系不甚美观,敬请谅解。
1.基本病史
超过60岁的男性病人,无特殊主诉。因体检发现“肝脏占位”入院。门诊查CT、MRI以及常规超声发现肝脏右前叶一大约5cm肿瘤,包膜完整。未发现肝内转移和远处转移。根据显像特点提示肝细胞肝癌。另发现肝脏轻度增大,边缘变钝,合并脂肪肝以及轻度肝硬化可能(图1)。既往合并症方面,有糖尿病、桥本氏甲状腺炎、高尿酸血症以及前列腺肥大等。无嗜烟、嗜酒史。查体未发现阳性腹部体征。
图1MRI显示位于S8的HCC,可见肿瘤包膜完整,左侧为被挤压的肝右静脉,但尚未被侵犯
术前检查:三大常规、肝肾功能、凝血常规、心电图、心肺功能、乙肝三对半无殊,肿瘤指标AFP正常,但PIVKA-II,显著升高。
总体印象:单发肝癌,伴脂肪肝以及可疑轻度肝硬化。
2.术前准备和评估
2.1肝脏储备功能评估
(1)Child-Pugh评分:5分。
(2)ICGR15:8。
2.2肿瘤的定位诊断以及切除范围的确定
2.2.1肿瘤定位和解剖变异情况的确认
(1)大体位置:S8;
(2)肿瘤供养支:P8背侧支的分支,经过并进入肿瘤(图2);
图2P8背侧支的分支为供养支
(3)肿瘤毗邻支:V8,与肿瘤较近,但未侵犯(图3);
图3与肿瘤接近的V8,未被侵犯
(4)门静脉、肝静脉、肝动脉和胆道未发现解剖变异;
(5)由此绘制解剖示意图(图4),最终肿瘤定位为S8背侧亚段。
图4笔者绘制的术前解剖示意图
2.2.2术前3D模拟手术
根据各种可能的术式,分别计算切除肝体积、剩余肝体积以及潜在的淤血肝体积等(图5)。针对S8的解剖性切除是相对简单的术式,但考虑到CT提示病人可能伴有轻度肝硬化,最终选择S8背侧亚段解剖性切除术。
图5术前3D模拟手术,图A显示S8Vent,图B显示S8Dorsal
3.手术主要步骤
(1)游离右肝,第二肝门,注意肝短静脉的处理(图6);
图6右肝的翻转,肝短静脉的处理
(2)肝十二指肠韧带预置阻断带;
(3)术中超声探查,了解肿瘤的位置,供养支与毗邻血管的确切关系,确认是否受侵犯;
(4)通过超声定位,拟定对P8背侧支注入ICG染色。但在术中超声检查发现P8背侧支位置较深,较难控制ICG注入速度,ICG很可能同时流入腹侧支,导致错误染色。因此决定通过“杀手锏”——反向对比染色法,即将P8腹侧支和P7先后染色,切除其间未被染色的区域,即为S8背侧亚段(图7);
图7用ICG对S8Vent以及S7先后进行荧光染色显影
(5)在肝脏表面用电到标记切除线,开始离断S8背侧亚段(图8);
图8电刀标记切除线
(6)阻断并切断、结扎P8背侧支主干(图9);
(7)切除标本,残肝断面露出V8主干(图9)。
图9离断S8背侧亚段
成功完成该术式的判定标准为:?残肝断面显露P8背侧支主干的断端;?残肝断面完全显露V8主干,且不允许损伤。
4.术后标本处理
(1)绘制出标本正反面的确切形态(图10);
(2)测量长宽高;
(3)标记肿瘤的位置,测量肿瘤的长宽高;
(4)标记P8背侧支断端结扎线的位置;
(5)切开标本,绘制剖面示意图(图10);
(6)送标本至病理科。
图10笔者绘制的标本示意图
5.感想——解剖性肝切除在东大肝胆胰外科的灵活运用和传承
5.1正确理解肿瘤和脉管的解剖关系是成功完成解剖性肝切除最基础、最关键的步骤;
5.2术中超声的作用无可替代,坚实掌握肝脏的超声解剖知识同样是成功和灵活完成解剖性肝切除的必备技能;
5.3关于解剖性肝切除的几点看法
近年来有不少临床研究比较了“解剖性肝切除”和“非解剖性肝切除”的优劣,结果是两者在对病人远期预后的影响方面“各有胜负”。笔者只是一名年资不高的主治医,通过本阶段在东大肝胆胰外科的学习所见和文献的阅读,粗浅地谈下对于该术式的看法。
(1)“解剖性肝切除”的由来和理论依据:该术式是著名的幕内雅敏教授在东京大学肝胆胰外科就任时大力倡导的,日语称作“系统性肝切除”。提出该术式的理论依据是肝癌的肝内转移方式:?侵入门静脉后向末梢播散;?通过动静脉短路向门静脉中枢逆流;?门静脉被癌栓堵塞后,向中枢逆流(图11)。因此,如能完整切除肿瘤所在的门脉供养支的肝脏体积,理论上即能达到根治。但是,受限于目前的影像学技术以及肿瘤示踪技术的水平,要在细胞和分子水平完准确观察到肿瘤在肝内的分布情况是不可能的。因此,即便进行了“解剖性肝切除”,仍会有肿瘤在其他肝段或亚肝段的复发或转移,两者对预后影响“优劣性”的比较确应进行长期随访、大样本的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后才能得出。但与单纯的“肿瘤核出术”相比,该术式在肿瘤学上仍然有明显的优势;
图11肝细胞癌的经门静脉转移模式
(摘自:上西纪夫,等.肝脾外科常规手术操作要领和技巧.;2:63.)
(2)与“远期预后”这个层面的比较而言,笔者个人认为“解剖性肝切除”的真正优势在于提高了手术的“安全性”。支撑起“解剖性肝切除”的四大法宝是“ICGR15”、“术前3D模拟肝切除”、“术中超声”以及“术中ICG荧光显影”。可以看出该术式是建立在“仔细分析肿瘤和肝脏脉管的解剖关系”、“充分了解肝脏储备功能”以及“实现肝切除可视化和术中导航”的基础上,因此会大大降低意外损伤肝实质内大血管和胆道,从而减少术中、后大出血、胆漏,肝脏淤血及腹腔脓肿的风险,而这些正是有助于提升手术安全性和加速病人的术后康复进程的关键因素;
(3)“解剖性肝切除”在针对肝癌伴局部转移或术后复发的病人具有较大的治疗优势,因为该术式完善的术前评估体系可较为科学地平衡“尽可能多地切除肿瘤所在的肝实质(治疗肿瘤)”和“尽量多地保留残肝的安全体积(保证肝功能不衰竭)”之间看似无法平衡的矛盾。另外,对于后一次手术的外科医师来说,也更容易理解前一次术后的残肝结构;
(4)该术式更有助于年轻医生的培养,对于提高他们对于肝脏解剖和生理知识的认识帮助很大。通过长期严苛的术前评估和术中实际操作训练,能保证年轻医师的临床技能扎实、稳步的进步,从而也使“解剖性肝切除”的全套理论和实践体系得以很好的传承。本病例手术中临时决定采用“反向对比染色法”即是在熟知解剖知识的基础上对“解剖性肝切除”的灵活运用。很难想象:在东京大学肝胆胰外科,此类高难度手术的主刀一般是年资不太高的病栋诊疗医(大约工作10年左右),负责术中超声、ICG注入、解剖肝门和脉管以及肝切除等关键步骤。而带组主任在术中的“职务”则是“指导的助手”,中文直译名为:起指导作用的助手(图12)。只有碰到意外以及操作难度极大的情况时,两者的位置才会互换。这也是为什么幕内雅敏教授早已退休离开东大,而“解剖性肝切除”至今仍被高水平地代代相传并在世界“威名远播”的原因。
图12手术记录首页显示的高难度第七次复发肝癌切除术的主刀和一助情况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