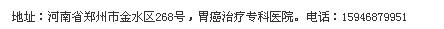《楊復再修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出版說明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
书籍名称: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
作者:(宋)楊復撰/林慶彰校訂/葉純芳、橋本秀美編輯
出版社: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出版年:-9
页数:
装帧:平装
ISBN:4
《楊復再秀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出版說明
葉純芳
一、前言
過去的朱子研究,偏重於理學哲學理論,禮學又走上所謂「漢學」一途,朱子禮學恰好處於不宋不漢的中間領域,導致乏人問津的窘境。雖然近來禮學研究逐漸興盛,朱子研究的範圍也擴展至禮學[1],並肯定儀禮經傳通解的禮學地位,如白壽彝、戴君仁兩先生將重點放在考證參與編纂儀禮經傳通解的友朋、門人上;上山春平先生討論朱子在編纂儀禮經傳通解前後的禮學思想的轉變等等。但他們討論的主要根據是朱子的文集與語錄,除了有關篇目結構的討論之外,幾乎完全看不到對儀禮經傳通解具體内容的分析,儘管他們眾口一詞地認爲儀禮經傳通解是朱熹最重要的禮學著作。究其原因,除了學術界向來缺乏分析像儀禮經傳通解這種經學著作的有效方法,文獻本身的問題無疑也形成一個很大的障礙。周予同先生論朱熹經學,即認為儀禮經傳通解是朱熹未完之作(喪、祭禮未完),又為通禮性質,「實不足以窺見朱子對於禮經之見解」(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本,朱熹,第四章,朱熹之經學禮經學)。試想,我們難道只能根據文集、語錄這些不成系統的言論,來討論其編纂過程以及朱熹的禮學,卻捨棄有完整體系的主要專著不論?筆者認爲,我們應該想辦法克服研究方法與文獻兩方面的問題,直接切入到儀禮經傳通解的内容,體味朱熹及弟子投入大量心血編纂此書的具體思想,不能永遠圍繞著儀禮經傳通解的外圍,空談概念。[2]
朱子的禮學,由儀禮經傳通解構築而成,這是無可置疑的。以往,學者以續編喪、祭二禮非朱熹所作爲由,不納入朱熹的禮學系統中討論。[3]事實上,未完成的喪、祭禮二禮,由他親手將此重任交給門人黃榦完成,並曾多次與黃榦討論喪、祭禮的規模架構。雖然黃榦僅完成喪禮,祭禮未脫稿即歿,但繼之有朱學的服膺者、黃榦的弟子楊復為二先師續完祭禮的工作。因此,喪、祭禮雖非直接成於朱熹之手,但其禮學思想絕對與朱熹息息相關。學者又謂,喪、祭二禮是朱子門人為求經傳通解之全,堆砌資料而成的資料集,故元代前期有胡庭芳云「三禮惟有通解,缺而未備者尚多,至門人勉齋黃氏、信齋楊氏粗完喪、祭二書,而授受損益精意,竟無能續之者」(送胡庭芳後序,熊禾勿軒集,卷一),元代後期有朱隱老說「儀禮經傳朱子以命勉齋黃榦,榦以屬信齋楊復,記錄雖詳而去取未當」(朱隱老傳,林弼登州集,卷廿一),都以爲蕪雜不足取。這些評論或許適合於楊復編次的黃榦稿本祭禮,而絕不適合於楊復再修之祭禮。
在看到楊復再修的祭禮之後,我們可以認為朱熹定本經傳通解(家、鄉、學、邦國禮)、朱熹稿本集傳集注(王朝禮)、黃榦喪禮、黃榦稿本祭禮及楊復祭禮五個部分結合起來,足以形成一套完整的禮書,以此視爲朱熹師門禮學之圭臬,并不爲過。雖然的確有如前人所批評,前面四部分理論結構性較爲薄弱,然今得楊復祭禮,猶如添加一塊支柱,五部分作爲整體,即使不免修補、重疊之跡,仍顯得宏偉而穩重。將此楊復祭禮公布於世,相信足以改變世人對經傳通解舊有的印象,進而能夠促使學界深入研究朱熹一門的禮學,同時也可以獲得分析禮學著作的新視角。當然,就祭禮的具體内容而言,本書的價值也非常突出,因爲明清朝廷有關禮制的重要討論,往往以本書爲理論基礎,只不過當時沒有人直接參考本書,都是通過文獻通考間接地利用本書而已。楊復這部書的學術價值是多方面的,遠非筆者能用簡短數語可以概括,因此迫不及待地想呈現給讀者。
以下,為行文方便與避免混淆,黃榦儀禮經傳通解續祭禮,簡稱黃榦祭禮;楊復重新編纂的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簡稱楊復祭禮,以示區別。
朱子
二、兩部不同的儀禮經傳通解續祭禮
儀禮經傳通解是朱熹晚年所修定的一部禮學文獻資料匯編性質的書籍。在此之前,他曾經因為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感到不滿,撰乞修三禮劄子,期待朝廷能夠重修三禮,終因「劄不果上」,於是晚年回鄉,集門下眾人的力量編成此書。嘉定十年丁丑()八月,時任知南康軍的朱熹兒子朱在刊行儀禮經傳通解三十七卷,其中前二十三卷(家禮五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爲朱熹所定本,題稱儀禮經傳通解;後十四卷(王朝禮)爲稿本,題稱舊名儀禮集傳集注,而喪、祭二禮闕如。
喪、祭二禮,朱熹生前曾託之於弟子亦為女婿的黃榦完成。[4]慶元六年庚申(),朱熹病歿,前一日仍致書與黃榦訣別(與黃直卿書),並叮囑其編成「禮書」(按:朱熹所謂「禮書」,指儀禮經傳通解,下文皆同)。朱熹選擇黃榦助其完成喪、祭二禮,亦有跡可尋,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年譜慶元二年丙辰()即云:
文公雖以喪、祭二禮分畀先生,其實全帙自冠、昏、家、鄉、邦國、王朝等類,皆與先生平章之。文公嘗與先生書,云所喻編禮次第甚善。
可見在編撰經傳通解上,黃榦深得朱熹的倚重信賴。嘉定十三年庚辰()夏,黃榦修訂喪禮十五卷成,將修祭禮,卻因「素苦痞氣」,十四年辛巳()三月,終于所居之正寢。
(一)兩部祭禮的形成與流傳
1.黃榦祭禮
未完成的祭禮,朱熹對篇目內容早有構想,原本的計畫是喪禮由黃榦編纂,祭禮由吳伯豐、李如圭編纂。在與吳伯豐的書信中,即有「祭禮嚮來亦已略定篇目」之語,並附上與李如圭商討的篇目順序,指示各篇收錄的材料(見晦庵集卷五二、五九)。後來吳伯豐過世,李如圭所編不合朱子意,最末,喪、祭二禮全都交給了黃榦。
從篇目來看,黃榦祭禮基本上是遵照朱熹的意思而稍事增刪修改,可知朱熹在世時,祭禮的規模已大致確定。雖然黃榦遵照朱熹的囑咐且態度極為認真,但由於「中間奔走王事,作輟不常」,導致二禮遲遲未能定稿。直到嘉定十一年十一月,「差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置局於寓舍之書室及城東張氏南園」,才得以重修儀禮經傳續卷。(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年譜)
嘉定十三年夏,喪禮成書,黃榦接著打算要修訂祭禮的稿本。年譜引楊復云:
祭禮亦已有書,本經則特牲、少牢、有司徹,大戴則釁廟。所補者,則自天神、地祇、百神、宗廟以至因事而祭者,如建國、遷都、巡守、師田、行役、祈禳及祭服、祭器,事序終始,其綱目尤為詳備。先生嘗言:「某於祭禮,用力甚久,規模已定。」
但最後因病未及完成。黃榦曾將此書稿授與楊復,曰「子其讀之」。楊復追憶並推測黃榦之意,是「蓋欲通知此書本末,有助纂輯也」,說明他生前曾想邀楊復共任此責。目前可見的四庫全書本儀禮經傳通解續祭禮的作者題為楊復,實際上內容是由黃榦所編纂的,只是「有門類而未分卷數,先後無辨」(楊復喪祭二禮目錄後序),於是楊復代黃榦做稿本的編次工作。
嘉定十六年癸未(),張虙於南康補刊喪、祭二禮,共二十九卷。其中喪禮十五卷,黃榦撰;喪服圖式一卷,楊復補撰;祭禮十三卷,黃榦撰稿本、楊復分訂卷次。黃榦這部祭禮,就是目前通行本的儀禮經傳通解續祭禮部分。楊復幫助編輯黃榦祭禮的具體情況,在其所撰喪祭二禮目錄後序、祭禮(黃榦祭禮)後序、祭禮(楊復祭禮)自序等文中有基本的説明。又,續修四庫全書收錄黃榦弟子陳宓的文集,幫助我們瞭解張虙刊刻黃榦喪、祭禮的更多細節。
元元統三年乙亥()六月,江浙等處儒學提擧余謙等「刊補」黃榦喪禮、祭禮,當即用張虙所刊書版歸國子監者(所藏版片元代歸西湖書院),修補印行。明、清所用,皆為此本;朝鮮、日本翻刻本,亦據此本。(關於黃榦喪禮、祭禮的詳細情況,請參看筆者另外爲影印傅增湘舊藏宋刊元明遞修本儀禮經傳通解撰寫的出版説明。)
儀禮經傳通解正續編
2.楊復祭禮
楊復,字志仁,福州人。生年不詳,據淳祐()六年十一月中書省劄「信齋楊先生復隱德不耀,歿已拾年」,則卒年約當在理宗嘉熙元年()前後。明朱衡道南源委錄有楊信齋事略:
公名復,號信齋,福州長溪人。從文公游,後卒業黃榦之門。真德秀知福州,創貴德堂于郡學以居之。著祭禮圖十四卷,儀禮圖解十七卷,又有家禮雜說附註二卷。(卷七)
楊復一生,並不像朱熹、黃榦都曾在朝為官,只是一個純粹的讀書人。僅在死後,因門人鄭逢辰將其所編撰之祭禮上呈朝廷,被理宗特贈「文林郎」。為了方便理解楊復其人,我們姑且引用道南源委錄匯錄其師友對楊復的評語:
楊志仁有過於密之病,陳德本有過於疎之病。
昨寓三山,與楊志仁反復所脩禮書,具有本末。若未卽死,尚幾有以遂此志也。(以上,文公語錄)
志仁最能思索,儘可講學。
見示仁說,考索極精,傳示朋友無不嘆服,但恨不得相與欵語,各究所藴耳。
志仁、謙之,孜孜不怠。
朋友寂寥,未有一人真能窺見涯涘,如志仁天資勁特,識見通敏,竊有望焉。(以上,黃勉齋文集)
志仁問學精深,服膺拳拳。(陳宓文集)
從老師與同門的描述,可以大略知道楊復是個極愛讀書、識見通敏、治學嚴謹的人,甚至到了讓朱熹有「過密之病」的評價。他常與朱、黃討論禮書,並受到黃榦極高的評價與同門師兄弟陳宓的欣賞。
如上所言,嘉定十三年(),黃榦將修祭禮,即以其書稿授予楊復,有意讓楊復通知此書本末,以助其纂輯祭禮。儀禮經傳通解續序云:
復受書(黃榦祭禮稿本)而退,啟緘伏讀,皆古今天下大典禮,其關繫甚重,其條目甚詳。其經傳異同,註疏抵啎,上下數千百載間,是非淆亂,紛錯甚眾。
自此以後,楊復「朝披夕閱,不敢釋卷」,想等待機會讓黃榦筆削。未料黃榦第二年就因病過世,「遂成千古之遺憾」。
嘉定十六年(),張虙補刊喪、祭禮,楊復被同門推舉,為黃榦祭禮編次。不過正如楊復所言,其中許多前後矛盾、應修改、刪補、加按語的條目,都在黃榦死後成了遺憾。楊復因此興起了重新修訂祭禮的想法,據鄭逢辰申尚書省狀轉述楊復語「蓋積十餘年而始成書」,於紹定四年()完書。
書成之後,一直是手抄本的狀態,在此期間,楊復祭禮也曾引起周圍學者的高度注意,如真德秀即稱此書爲「千載不刊之典」。比起真德秀這句話更有具體意義,而且影響深遠的是衛湜曾將楊復祭禮的部分内容收入其巨著禮記集說中。按:衛湜於寶慶二年()撰成集說,紹定四年()亦即楊復撰成祭禮的那一年刻梓印行。之後九年的時間,衛湜繼續增訂集說,孜孜不倦,「倘佯於書林藝圃,披閲舊帙,搜訪新聞,遇有可採,隨筆添入」(禮記集說後序),至嘉熙三年()重新刊刻增訂新版,此時楊復已去世兩三年。今本衛湜集說,於卷首「集說名氏」列「秦溪楊氏復,儀禮經傳通解續祭禮十二卷」(按:應為十四卷),書中引用多條楊復的議論,當即在紹定四年至嘉熙三年之間,衛湜「搜訪新聞」所得。
淳祐六年(),楊復的門人鄭逢辰連同儀禮圖,各繕寫一部奉進,理宗下詔「付太常寺收管,以備參稽禮典」,這已經又過了十多年的時間。而方大琮寫給鄭逢辰的一封信,似乎透露鄭逢辰在上書之後不久,曾經單獨刊刻過此書:
某伏蒙委貺書籍四種,内楊信齋祭禮,則户部向嘗上之送官,今又進之乙覽,遂備儀禮通解全書。以書樓延致考訂十餘年而後成,又繕寫送進鋟梓十餘年而後傳,不孤信齋之勤勞,户部之力也。非特為信齋也,勉齋之目可瞑,考亭之志始遂。西山嘗稱其為千年不刊之典,信然。某曩得南康祭藁,今與此可以合觀。
「今又進之乙覽」,當指鄭逢辰淳祐六年繕寫奉進祭禮之事;祭禮紹定四年撰成,至淳祐六年奉進,亦符合「十餘年而後傳」之語。不過真相如何,仍有待更多的資料來證明。
而後,寶祐元年(),時任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的王佖因嘉定年間的儀禮經傳通解、通解續書版被國子監取去,提議在南康重刊儀禮經傳通解全書,祭禮則改用楊復所撰:
嘉定閒,嗣子侍郎公在方刻之南康郡學,後來勉齋黃公續成喪、祭二禮,亦併刻焉,而書監竟取之以去。曾幾何年,字畫漫漶,幾不可讀,識者病之,蓋懼此書之無傳也。佖乘軺東江,因敂本司發下之券尚存,遂即籌度命工重刻。爰首諮於堂長饒伯輿甫,牕契所懷,議以允協,且輟餐供餘鏹以助。遂囑其事於教官丁君抑,而任其讐校於洞學之善士,邦侯傃軒趙公希悅亦佐其費,復斡旋本司所有以添給之。志意既同,始克有成。迺就置其板於書院,庶幾藏之名山,或免湮墜。其經之營之,亦甚艱矣。然朱子所成三禮止二十餘秩,而勉齋所續則又倍之。厥後信齋楊君始刪其祭禮之繁複,稍爲明淨。今喪禮則用勉齋所纂,祭禮則用信齋所修。…(云云)…寳祐癸丑冬日南至,後學金華王佖端拜敬書。
雖然我們只能從愛日精廬藏書志看到張金吾據元抄本迻錄的王佖、丁抑、謝章三人的跋語,但記載詳細,是唯一可以說明楊復祭禮成為刻本的證據。
入元後,祭禮可能有覆刻本,內容也被當時的學者引用,如:陳師凱書蔡氏傳旁通,此書的「引用書目」即有「楊信齋祭禮通解」,是與「儀禮經傳通解」分列的。書中引用祭禮內容共三條,且全出自於楊書的「祭服」。又如:方回的桐江集中,亦出現此書部分的內容:
由祭禮而詳文公之言之意。郊祀天地,當南北分祭,而合祭非也;廟制當大祖之向左右分昭穆,而同廟議室以西為上非也。(讀朱文公儀禮經傳跋)
這些微乎其微的元人引文,都是極為珍貴的研究資料。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文獻通考。通考中有關「祭禮」的部分,馬端臨摒棄前人之說,全面採用楊復整理的理論體系。這是至目前為止,我們所看到保存楊復祭禮最多的古代文獻。不過,馬氏依據文獻通考的編排體例,將此書全部打散割裂,安置於不同類別下,欲窺此書之全貌,實屬不易。
明代雖未見有引用楊復祭禮者,但觀各種書志所言,並未與黃榦祭禮混為一談。
元代以後至清,祭禮的內容全都仰賴文獻通考才得以繼續流傳下來。凡是引用楊復語者,幾乎皆轉引自文獻通考,如清秦蕙田的五禮通考、黃以周禮書通故。而江永禮書綱目序有「黃氏之書,喪禮固詳密,亦間有漏落,祭禮未及精專修改,較喪禮疏密不倫。信齋楊氏有祭禮通解,議論詳贍,而編類亦有未精者」云云,或見過楊復此書。
今觀靜嘉堂藏本楊復祭禮,在元代經過補版,有的版面磨損嚴重,可見在元代印數不少。不過嘉定刻本入國子監,經余謙等修補,一直到明代國子監仍然邊修邊印,印數極多,非楊復祭禮可比。以至明正德劉瑞抽取經文刻本、清初梁氏重編刻本、清初呂氏刻本、四庫全書抄本等,祭禮部分用的都是黃榦的本子,楊復的本子遂被遺忘。
儀禮經傳目錄
(二)兩部祭禮的混淆
由於黃榦祭禮也曾經過楊復的編訂,黃榦原稿與楊復再修,兩部截然不同的祭禮,最後被不少學者混淆。先看明代以前有關此書的記載,如郡齋讀書附志云:
儀禮經傳通解續纂祭禮十四卷,右朱文公編集,而喪、祭二禮未就,屬之勉齋先生。勉齋既成喪禮,而祭禮未就,又屬之楊信齋。信齋據二先生藁本,叅以舊聞,定為十四卷,為門八十一。(卷五上,宋趙希弁)
如內閣藏書目錄的記載:
儀禮經傳通解續,宋淳祐間,信齋楊復著。……,凡十四卷,八十一門。是祭禮一書至此始大成也。(卷二,經部,明張萱)
又如明曾棨對編次的記載:
以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為經,冠之祭禮之首,輯周禮、禮記諸書,分為經傳,以補其闕。綜之以「通禮」,首之以「天神」,次之以「地祇」,次之以「宗廟」,次之以「百神」,次之以「因祭」,次之以「祭物」,次之以「祭統」,有變禮、有殺禮、有失禮,並見之篇終。(經義考所引,卷一百三十二,儀禮三)
這三條記載都針對楊復祭禮而言,與黃榦祭禮的情況完全不同。
然而四庫館臣不知祭禮有二,僅據黃榦祭禮討論問題,因此出現一系列錯誤論斷。如四庫全書考證對經義考的考證,即以上引曾棨說爲誤:
曾棨曰:「次之以宗廟,次之以百神,又次之以祭物,次之以祭統。」案:續儀禮經傳通解篇次,百神在宗廟上,祭統在祭物上。所引曽棨説誤。
翁方綱經義考補正所引丁杰說與考證同。上所言「續儀禮經傳通解篇次」,是根據黃榦祭禮,而曾棨所云,乃據楊復祭禮,篇次本來不同。丁杰僅知其一不知其二,遂以不誤爲誤。
四庫全書收錄黃榦的喪禮、祭禮,而提要將楊復祭禮與黃榦祭禮混爲一談:
其後楊復重修祭禮,鄭逢辰進之於朝。復序榦之書云「喪禮十五卷前巳繕寫,喪服圖式今別爲一卷,附於正帙之外」,前稱「喪服圖式、祭禮遺稿尚有未及訂定之遺憾」,則別卷之意固在此。又自序其書云:「及張侯虙續刋喪禮,又取祭禮稿本,併刋而存之。竊不自揆,遂據稿本,參以所聞,稍加更定,以續成其書,凡十四卷。」
「鄭逢辰進之於朝」,「竊不自揆,續成其書」,皆謂楊復祭禮,非黃榦祭禮。然黃榦祭禮十三卷,與楊復自序稱十四卷顯然牴牾,於是提要提出彌縫之說:
今自卷十六至卷二十九,皆復所重修。
其實卷十六是楊復補撰喪服圖式,在黃榦喪禮十五卷「正帙之外」,與祭禮更無關聯。今提要意欲將喪服圖式一卷并黃榦祭禮十三卷,以合楊復祭禮十四卷之數,不得不謂牽強。
至於內容的差異,陸心源云:
以呂留良刻本校之,脫落羼錯,妄刪妄增,竟無一合。以卷二少牢饋食禮一篇言之,……大約無一條不增改,無一葉無羼錯。呂留良謬妄至此,明季國初,竟負重名一時,時文鬼附之如雲,致蹈滅門之禍,殆有以也。(皕宋樓藏書志,卷七)
其實,陸心源拿楊復祭禮校呂氏所刊黃榦祭禮[5],「竟無一合」乃事理自然。陸心源後來也發現了自己的錯誤,在光緒十八年刊的儀顧堂續跋中作了以下的說明:
張虙所刊,乃信齋受于勉齋之稿本,即四庫所收、呂氏所重刊者。此則信齋以稿本修定者,與張刊本不同。故以呂刊互勘,或增或刪,或改或易,竟無一條全同也。張刊之板,明中葉尚存南監,惟缺頁斷爛甚多。此本則流傳極少,朱竹垞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二續儀禮經傳通解下不載逢辰序,又不載進表、中書省劄、理宗贈敕,則亦未見此本矣。惟趙希弁讀書附志、張萱內閣書目所箸錄,其言與此本合,所見當即此本也。(儀顧堂續跋,卷二)
從皕宋樓藏書志「妄刪妄增,竟無一合」到儀顧堂續跋「或增或刪,或改或易,竟無一條全同」,陸氏才恍然明白祭禮有兩種版本,是楊復的全面改寫,不是呂氏的「謬妄」。呂氏平白被陸心源責難,儀顧堂續跋竟也無一語說明。因此,簡明目錄標注移錄黃紹箕批語,直接抄錄皕宋樓藏書志的錯誤論述。只有胡玉縉先生四庫提要補正,並錄皕宋樓藏書志與儀顧堂續跋,做了準確的判斷:「跋語是,志蓋未定之說。」
後來日人阿部吉雄在一九三六年撰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經部禮類善本述略[6],其中一節專論儀禮經傳通解,全面釐清事件始末,他說:
儀禮經傳通解及續之編纂非出一人之手。特需注意者,續祭禮部分因著者之異,後世之刻本乃有二系統存焉。即黃榦之祭禮外,另有楊復之祭禮,二書之内容組織全異。前人或於此未能了然,遂至誤解叢生。
並為呂氏寶誥堂刊本所蒙受多年的不白之冤做了澄清:
此乃以黃榦之祭禮與楊復之祭禮對校之結果。然其誤不在呂氏刊本,而在校者自己。
黃榦
從以上所引書志來看,推測兩部祭禮是從清代開始被混為一談。經義考將楊復儀禮經傳通解續序部分的內容、宋趙希弁語(見上文)誤置於「黃氏榦續儀禮經傳通解」條下,而「儀禮經傳通解續十四卷」條下,僅錄明張萱語(見上文),應為淆亂二祭禮之始;四庫全書之誤,如上所述,而影響最鉅。又如道光時,陳金鑑輯宋黃度周禮說,曾根據文獻通考輯楊復祭禮引黃度周禮說的內容,陳氏按語云:「案此條通考兼引信齋楊氏續經傳通解,今本通解脱。」實則非今本通解脫,而是陳氏所見為通行本的黃榦祭禮。
此外,楊復祭禮不論在版式或內容編排上都與儀禮經傳通解幾乎相同,書成後仍名為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在無法看到此書的前提下,要讀者聯想到是不同的兩部祭禮,其實相當困難。當寶祐元年()重刊經傳通解時,選用的是楊復所撰的祭禮,原本是說明兩部祭禮完全不同的最好時機,但主其事者王佖,自己恐怕連經傳通解的內容都沒看過,王佖序說:
朱子退居燕閒,姑自稡錄,分吉、凶、軍、賓、嘉五禮,而條目燦然。僅成三禮而猶有未脫稿者。
朱熹經傳通解的五禮,分為家禮、鄉禮、學禮、邦國禮與王朝禮,加上未完成的喪、祭二禮,共有七禮;而王佖誤以為五禮是吉、凶、軍、賓、嘉,又僅知喪、祭二禮未成,故言「僅成三禮」。其中又有一段曖昧不明的話:
厥後信齋楊君始刪其祭禮之繁複,稍爲明淨。今喪禮則用勉齋所纂,祭禮則用信齋所修。(以上,引王佖序據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四)
讓後人誤會黃榦未完成的祭禮經過楊復修訂,因此選用楊復修訂的黃榦祭禮作為此次刊刻之依據。實際上,寶祐重刊所用的祭禮,與黃榦祭禮無關。若王佖當初願意多說一句類似「楊君重撰祭禮」的話,後人也不會誤解至此。
通觀歷代書志著錄,目前最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所著錄「儀禮經傳通解續二十九卷影寫元刊本」:
宋黃榦撰,卷十六至末則楊復所重修也。此本從元元統補刊本影寫。
其後收有王佖、丁抑、謝章等三人序。此三序內容,應為寶祐年重刊時所有,但經傳通解諸版本(包括靜嘉堂本楊復祭禮)皆不具此,僅見於張金吾所藏「影寫元刊本」中。按張金吾的描述,此抄本所自當是後歸國子監的嘉定舊版,卻有王佖等三序,不知其來歷如何。
又,上海古籍、安徽教育版朱子全書引錄王、丁、謝三序,皆據天一閣藏明抄本,據云僅存二冊。檢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此本存卷一、卷二及續卷六至卷八。不知其續卷六至卷八是否楊復所撰祭禮。
三、靜嘉堂文庫所藏楊復再修儀禮經傳通解續祭禮
(一)版本概況
靜嘉堂文庫所藏此本,原是明代項元汴(號墨林子)天籟閣的舊藏,後展轉到了陸心源的皕宋樓。民國初年,陸氏子孫因各方因素,不能守父業,皕宋樓所藏全部的宋元版書以當時的十二萬元賣給了日本三菱集團負責人之一的岩崎彌之助,岩崎氏並將此批宋元版收藏在他所創設的靜嘉堂文庫中。這段歷史,眾所周知,不多贅述。楊復祭禮,也就跟著一起到了日本。
日本靜嘉堂藏(原皕宋樓藏)楊復《儀禮經傳通解續卷》書影
陸心源儀顧堂續跋說此本是宋淳祐刊本,僅以卷首附錄鄭逢辰上表、敕等公文有淳祐六年、七年等時間,逕以爲刊年,別無根據。靜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錄解題篇著錄為:
儀禮經傳通解續祭禮一四卷卷首目一卷(有缺)
宋楊復撰元刊明初印本一五冊
其下按語云:
此書的字樣版式與宋嘉定刊本、元代元統三年修補的儀禮經傳通解相似;出現在祭禮的刻工姓名,同時也出現在元修的儀禮經傳通解中。
又謂:
本版避宋諱之處甚多,自當出於宋版,只是無法確定是宋版元修,還是元代覆宋版。幾乎每葉都有刻工名,都是元代刻工,連版面漫漶、刊彫時間應該離刷印時較久的版片,上面能看到的刻工名還是元代刻工。因無其他傳本可對比,姑且依據刻工名,著錄爲元刊本。
圖錄的上述説明,基本上都遵從阿部隆一日本國見在宋元版本志經部的説法。在沒有看到其他傳本的情況下,筆者認爲圖錄的判斷是妥當的。
需要強調的是,無論是版式特點、刻字風格,此本與嘉定年間朱在、張虙所刻儀禮經傳通解正續編一模一樣,而且此本所見刻工又都見於嘉定刻儀禮經傳通解的元代補版,這兩種書的外在特點完全一致,這就無怪乎舊京書影誤將此版著錄爲嘉定版(祭禮用黃榦本)。可是,分析刻工的結果顯示,此本書葉大都可認定為元代刻版,似乎不存在宋代刻版,只能認爲此本非元覆宋版,即宋版元修。至於此本所出宋版之種類,則有可能是淳祐間鄭逢辰的單行刻本(如陸心源所云),也有可能是寶祐間王佖的經傳通解正續合刻本。當然,也不能否定有第三種宋刻本的可能性。
圖錄又云:「此本(案:靜嘉堂藏楊復祭禮)標題『續卷第幾』,卷次自一起,未與喪禮通數卷次,明此本爲祭禮單行本。」然雙鑑樓舊藏宋版儀禮經傳通解續(嘉定舊版元明遞修本)卷首目錄前有兩行識語云「喪、祭二禮元本未有目錄,╱今集爲一卷,庶易檢閲耳」(日刊本同),當是元代元統年間,余謙等人修補舊版時所爲。嘉定十六年南康始刊喪禮、祭禮時,稿本祭禮未分卷,楊復受託分訂爲十三卷,楊復祭禮自序亦云「及張侯虙續刊喪禮,又取祭禮稿本併刊而存之」,蓋嘉定十六年南康始刊本,喪、祭二禮分別爲卷次,未將喪、祭統訂卷次,現存傳本每卷首行題「續卷第一」至「續卷第二十九」者,出元統修補時。果真如此,當寶祐重刊時,祭禮改用楊復書,喪禮、祭禮撰者不同,更無需通數卷次。因此,卷次是否通數,並不能作為是否單行本的證據。所以上文提出此本或其底本的宋版種類有三種可能性,都不能排除。
陸心源
此書目次題名為「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目錄」,書內每卷首行的題名為「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第幾」,每半葉七行,行十五字,注文雙行,行十五字。有「天籟閣」、「項墨林鑑賞」、「墨林祕玩」、「昌」、「南陽講習堂」、「歸安陸樹聲叔桐父印」、「臣陸樹聲」等印記。
每卷皆有闕葉,卷十四僅至「祭禮七十五」止,「卜筮」至「變禮」(祭禮七十六至八十一)皆亡佚。漫漶、補版的情況亦不少,補版不一定仍以行十五字為原則,有時十六字,亦有行十七字。所幸祭禮中最重要的天神、地示、宗廟等篇都大致完好。
因為歷時久遠,避免不了重新裝幀,而導致葉數錯置的情況;又因為錯置,而將葉數描摹成裝幀者以為的葉數,我們只能在抄錄、整理的過程中,根據前後文的銜接,一一還原其位置。
本書第一册為序、目。不同於一般常見古籍的編排,此版本從第一卷開始的版心處,葉數上方有一個漢字作為標識,每卷的漢字都不同,將各卷依序排列:
雖有闕字,但仍可以得出一首五言絕句:
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
這首詩出自南史陳本紀,是陳後主叔寶被俘虜後,在一次從侍隋文帝出巡時所寫的一首詩,被後人解讀為陳後主諂媚隋文帝所作的告白,文苑英華題名為入隋侍宴應詔。(按:「東封書」亦有作「登封書」者,此本恰好闕十三卷下的標識,仍依南史所記作「東」。)歷代五言絕句多如牛毛,何以獨鍾意此詩作為標識順序之用,原因不明。此詩二十字,正與鄭逢辰上書云「繕寫為二十帙」相符,不知當初是否即據此分册?這些標識是宋代初刻時即有,還是元代覆刻時才有?則無法驟下定論。不過,據宋朱翌猗覺寮雜記所言:
「日月光天德」云云,陳後主國亡入隋,從隋文東封,登芒山所獻詩也。天下敎兒童者,以此題學書紙。(卷上)
宋曹士冕撰法帖譜系又云:
世傳潘氏析居法帖石分而為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一,於是補刻餘帖,是名「東庫本」。……且逐卷逐段各分字號以『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何以報,願上登封書』為别,此又異於舊帖也。(卷下)
大約自北宋開始,此詩便常用來作為標識順序之用了。因為本書目錄、正文皆有缺葉,有了這首詩,在整理的時候,更能清楚地了解整部書的殘闕情況。靜嘉堂目前的分冊,其實也不與「日月」二十字的分法相矛盾,只是目前的第八冊、十二冊、十三冊、十四冊,原來應該分別作爲二冊,後來被合訂爲一本。又,在有標識字的卷中,亦見無此標識字之葉數,都可作為討論是否為補版之參考依據。
(二)內容與價值
書共十四卷,八十一門。楊復基本依照朱熹經傳通解與黃榦通解續的作法,「正經在前,補編在後」。正經,指卷一儀禮經上特牲饋食禮、卷二儀禮經下少牢饋食禮(有司徹附);補編,則指卷三通禮篇以下至最末卷,蒐輯周禮、禮記諸書與祭禮有關條文者,分為經、傳兩部分。並按照朱熹經傳通解冠禮後有冠義,昏禮後有昏義的作法,隨類分之,不過考慮到「祭禮綱條宏闊,記博事叢,若以祭義盡歸於後篇,則前後斷隔,難相參照,讀禮之文不知有其義,讀禮之義不知有其文」,因此,做了些微的調整:「凡傳記論郊之義者附於郊,論社之義者附於社,論蜡之義者附於蜡,……。」(儀禮經傳通解祭禮義例)也就是說,由於祭禮的條目較為繁瑣,若按照經傳通解冠禮全文結束後才有冠義的作法(黃榦祭禮最後一卷亦為祭義),則禮文與禮義無法貫通,於是楊復在不違背通解體例的前提下,於補編採取每卷細分為多條子目,如天神篇,又分為祀昊天上帝禮、明堂禮、正月祈穀禮、孟夏大雩禮、祀五帝禮、祀五人帝五人神禮、祀日月星辰禮、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禮等,凡傳記中有言及各禮之義者,皆分屬於各禮下。使條目清晰,同時也能貫通文義。
雖然楊復很保守地在序中說:「竊不自揆,遂據稾本,參以所聞,稍加更定,以續成其書。」實際上從編次到內容,與黃榦的祭禮相較,出入頗大。不過,楊復即使是重寫祭禮,還是必須承認他是在黃榦祭禮的基礎上撰成此書,而非自己創作的。理解這個前提,我們看看關於兩部祭禮編次的不同,列表如下:
楊復在儀禮經傳通解祭禮義例當中,特別說明少牢饋食禮與有司徹合為一卷的理由,是本之於鄭玄:「鄭目錄云『有司徹,少牢之下篇也』,故併而合之,以為一篇。」從此處與各卷經文下皆先錄鄭注來看,可以說明楊復在解經的立場上與朱熹通解同尊鄭注。
除「正經」之外,在「補編」內容的安排上,則根據禮之重要先後為次(參見楊復儀禮經傳通解續序)。其中相當引人注意的是「正經」之後、只有五葉的卷三──通禮篇。雖名之為「通禮」,實際上性質與我們認知的「通禮」定義不太相同。它有「義界」的作用,說明楊復認知的祭禮規模;亦有「正名」的作用,說明祭禮的內涵;又有「提綱挈領」的作用。通禮一篇,集中表述楊復對祭禮的基本立場,可以説是整部祭禮的開宗明義篇。
在經注疏與史材料的取捨上,楊復並非簡單地迻錄與堆砌,以三禮疏來說,大部分的賈疏、孔疏都經過他細心的剪裁與編纂。同時,也可以從這些裁剪看出他的立場,通禮篇云:
愚案:通禮一篇,通論天神、地示、人鬼之禮也。然先王制禮,抑又有深意存焉。周官大宗伯以禮佐王者凡十有二條,而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為先。蓋禮莫重於祀天,冬日至,祀昊天上帝於地上之圜丘,惟王得行之也。禮經又兼言「天子祭天、地」者,蓋王者事天明事地察,尊天親地,敬無不同。夏日至,祀皇地祇於澤中之方丘,亦惟王得行之也。自是而下,諸侯得祭社稷而不得祭天地,大夫得祭五祀而不得特立社稷,凡此皆所以明天下之大分,立天下之大經也。宗廟以下皆放此。(卷三)
禮莫重於祀天,而不論是祀昊天上帝,或祀皇地衹,「惟王得行之」。體現他尊王的基本立場。
且看他如何在細節的處理上都貫徹這種基本立場:如天神篇明堂禮引禮記明堂位云:「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鄭注:「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户牖之間,於前立焉。」(卷五)前文有言,楊復尊鄭注,引用三禮經文幾乎全錄鄭注,但在此處,他對鄭注進行重大刪節。鄭注原文是:「天子,周公也。負之言偝也,斧依爲斧文屏風,於户牖之間,周公於前立焉。」兩相對校,可見楊復刪掉兩「周公」,意指天子就是天子,而非周公。對楊復來說,周公以攝政的身分居天子之位,於「惟王得行之」不合,所以特加按語,明言「此說舛謬,故削去之」。至若在天神篇祀昊天上帝禮引孝經「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注:「周公行郊天之祭。」(卷四),玄宗注原作「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祭」,楊復逕刪「攝政因」三字,無任何説明,顯然也出於否定攝政的原則性考慮。
在編纂的態度與資料的蒐集上,除以黃榦祭禮做為藍本,可能還從黃榦處借得相關禮書與朱熹的語錄、文集等資料。又據鄭逢辰申尚書省狀引楊復語云:「研精覃思,蒐經摭傳,凡日湖所藏之書,繙閱殆遍。蓋積十餘年而始成書。」按朱熹弟子閩縣鄭昭先,號日湖,為楊復弟子鄭逢辰之父。楊復所言「日湖」或即此人。大致可推知楊復自己的藏書並不多,需藉助同門、朋友家中所藏書。
本書之可貴,對藏書家來說,或許是因為世上僅存此本,不過對研究宋代禮學、朱子學派禮學思想的學者來說,全書約一百三十條的楊復按語,才是本書最大的價值所在。這些按語,有釋義、釋名物;有糾謬、斷是非。其中亦不乏近三千字,對「禘祫禮」的看法,這也是與黃榦祭禮僅錄經注疏文最大的不同之處。
其次,楊復祭禮所引用古今諸儒之說(參見儀禮經傳通解祭禮義例),其中「曰『黃氏』,則山陰黃度,先師同時之賢」者,黃度的周禮說已亡佚,今可見者,為清陳金鑑根據文獻通考等書所輯之宋黃宣獻公周禮說(文獻通考所錄者,亦引自楊復祭禮),兩相比對,有楊復祭禮有而陳輯本所無者;而「曰『陳氏』,則門人三山陳孔碩,嘗問釋奠儀」者,則有數條均已不見於今存古籍中。又引用隋唐時期潘徽的江都集禮,此書今已亡佚,但由陳宓寫給楊復的信云:「昨所傳江都禮,今附陳戊拜納,此間無他本可校,萬一得暇,因乞是正,以惠學者,亦一幸也。」(與信齋楊學錄復書,陳宓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可說明楊復祭禮所錄,非轉引自他書,而是直接參考江都集禮原書。又如李如圭儀禮集釋,雖然有輯自永樂大典的四庫本,世人多以爲已得其全,但本書所引往往出四庫本之外,可以補正者不少。可說此書不論在禮學思想上或文獻價值上,都有極大的貢獻。
以上,是靜嘉堂文庫所藏本的大致情況。
目前,我們亟於知道的是楊復祭禮是否還有別本存世?是否真如阿部吉雄所言,此本是「天下孤本」?在抄得楊復祭禮後,我們也嘗試在臺灣、日本、北京等地圖書館,以及已出版的漢籍善本書目上尋找此書其他本的可能性,很可惜尚未發現。即使如此,情況不如我們想像地絕望。阿部隆一早已注意舊京書影所收書影是楊復再修的十四卷本祭禮,並且與靜嘉堂本進行對比,認定所用版片不同,是不同時期印本。我們後來在宋元書式中也找到一張書影,按内容可以確定是楊復祭禮,行格安排與靜嘉堂本相同。
舊京書影、宋元書式都是在一九○七年皕宋樓將宋元版書賣給了靜嘉堂文庫之後編纂的(參見舊京書影、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出版說明,年1月,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版本目錄學書籍解題,長澤規矩也編著,梅憲華、郭寶林譯,年6月,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可以確定這兩幅書影與靜嘉堂所藏的並非同一本書。那麼,書影中的祭禮是一部還是兩部?現在在哪裡?由於臺灣與日本所藏之中國古籍大致上都已著錄出版,我們推測比較有可能出現的地方應該在中國大陸,或許隱匿在某個圖書館所藏的經傳通解之後,或許仍為私人所藏書。無論如何,我們衷心希望藉此次出版的機會,能拋磚引玉,找到祭禮的其他本,補足此本殘闕、漫漶之處。這是我們這次整理出版楊復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的另外一個重要目的。
四、從楊復祭禮勾勒出一條禮學脈絡
周禮春官大宗伯將禮儀分為吉、凶、賓、軍、嘉五禮。吉禮,是向天神、地衹、人鬼祈求,保佑人們諸事如意安康,故稱之吉禮,亦即是祭祀之禮。禮記祭統云:「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左傳成公十三年有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說明較之於其他禮儀,祭禮顯得尤其重要。雖然朱子說:「禮,時為大。有聖人者作,必將因今之禮而裁酌其中取其簡易易曉而可行,必不至復取古人繁縟之禮,而施之於今也。古禮如此零碎繁冗,今豈可行?亦且得隨時裁損爾。」(朱子語類,卷84)但我們從歷代文獻中卻發現祭禮越來越紛雜繁瑣,學者的解說也益見分歧。
漢代以來,祭禮習俗與經學之間一直存在糾纏不清的複雜關係。祭祀本諸人心,時地不同,祭祀也相異。而且經書的形成晚於祭祀的發生,因此不同經書中散見的記載之間,經常出現互相矛盾的內容。如何解釋這些矛盾,便是經學家必須解決的理論問題。
歷代經學家都曾提出各種理論體系,對後世產生或大或小的影響,但學者歧見始終未能達到統一。其中鄭玄、王肅的理論體系,成為後世學者無可迴避的議論前提,而朱熹禮學對元、明、清三代的影響,不在鄭、王之下,無疑是最重要、最值得重視的。但理論僅僅是問題的一半,還有一半是現實的祭禮習俗問題。無論在漢代還是在宋代,現實的祭禮習俗與經學理論之間都存在巨大差異。如何調和其間差異才算理想,各種因素之間如何平衡為最現實可行,都是非常複雜的問題,容有無數種不同的答案。分析不同朝代不同學者、朝臣提出的不同答案,探討他們不同的思考習慣,是祭禮研究的關鍵所在。
(一)朱熹禮學的形態
由前文的分析,說明我們不僅可將祭禮視為楊復的禮學思想,同時也可視作朱熹一派禮學思想的根據。身為朱熹的弟子,楊復在主觀上期望能全面反映朱熹的祭禮理論。
朱熹之禮學,錢穆朱子新學案[7]已經有精要的綜述。簡言之,自從王安石罷廢儀禮之後,導致士人僅知有禮記,不知有儀禮。而誦讀禮記,只為了應付考試。朱熹認為,三禮學是實用之學,可成為朝廷制禮的依據,偏安的南宋朝廷的確也需要一套完整、有系統的禮制來撫慰飄搖的人心。然而當時的實情卻是朝廷每有大議,博士諸生僅憑聽聞所得加以臆測而無所本,所有儀節之所以立者盲昧無所知。因此朱熹想編修禮書以供「聖朝制作之助」(乞修三禮劄子)的念頭在中年時期已開始萌發。
朱熹晚年,在答李季章書(慶元四年,)中説明禮書的概況:
大要以儀禮為本,分章附疏,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它篇或它書可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又其外如弟子職、保傅傳之屬,又自别為篇,以附其類。…………今其大體已具者,蓋十七八矣。因讀此書,乃知漢儒之學有補於世教者不小。如國君承祖父之重,在經雖無明文,而康成與其門人答問蓋已及之,具於賈疏,其義甚備,若已預知後世當有此事者。
所言「國君承祖父之重」的例子,是朱熹切身的體驗。紹熙五年()孝宗去世,寧宗即位,朱熹撰劄子議寧宗當服斬衰三年。當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時無明白證驗」,「歸來稽考,始見此説(按:賈疏所載鄭志說),方得無疑」。(乞討論喪服劄子後附書奏稿後)是知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為主,輔以禮記等經典文句,附錄註疏之說可補經傳者,旨在為討論當世禮制時提供全面可靠的經典依據。既非以此書為可施今世的禮典,又非彙編歷代禮制、禮議之大全。因此,熊禾在元初稱朱熹還想將「通典及諸史志、會要、開元、天寶、政和禮斟酌損益,以為百王不易之大法」(刋儀禮經傳通解,勿軒集),未必得朱熹本意。
朱熹另撰有一部家禮,是一部生活實踐禮儀的著作。要討論朱子的禮學,應通過家禮與儀禮經傳通解。但歷來的討論者,往往將這兩部書分別看待,甚至因為兩部書的性質迥異,而對家禮產生質疑。其實,朱熹對生活實踐禮儀的看法,相當靈活。如與上引答李季章書同年的語錄中有人問「用僧道火化」,朱熹答曰:「其他都是皮毛外事,若決如此做,從之也無妨,惟火化則不可。」雖然重要原則不能讓步,但細節問題不妨隨俗。在朝議禮,必須在現有禮制文化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意見;在地方做官或做士紳,只能想辦法改善士紳以及庶民的禮俗。於是,作爲經學理論根據的儀禮經傳通解,與作爲實踐禮俗方案的家禮,不得不各自獨立成編。經傳原文、漢人注說、唐、宋人的經說、歷朝的議禮以及當代朝廷的爭議、當世民間的禮俗,還有朱熹自己的禮文化理念等等,諸多不同方面的因素互相矛盾,在朱熹心中自然會有統一理解的系統。但當他訴諸文字,著書立說,還是無法形成一體。
(二)楊復以經學理論統馭禮制問題
當楊復從黃榦手中接下祭禮稿本時,直覺祭禮的內容「皆古今天下大典禮」、「關係甚重」、「條目甚詳」,但細讀之後才發現「註疏抵啎」、「是非淆亂」、「紛錯甚眾」,突顯出歷代禮學的矛盾,此時的楊復,開始有了重新撰寫祭禮的想法。
重新編寫的祭禮,雖然在體例上、內容編排上都承襲經傳通解的精神,但在面對歷代材料的取捨卻有很大的不同,對「歷世聚訟而未能決者」,如明堂、南郊、北郊、古今廟制、四時禘祫等問題,都做了深入的探討與檢擇處理,並做出自己的判斷,「使畔散不屬者悉入於倫理,厖雜不精者咸歸於至當」(申尚書省狀,鄭逢辰引楊復語),形成自己一套祭禮理論體系。宋人對鄭玄解經多所批評,他卻持肯定的態度:「鄭康成注儀禮、周禮、禮記三書,通訓詁,考制度,辨名數,詞簡而旨明,得多而失少,使天下後世猶得以識先王制度之遺者,皆鄭氏之功也。」(祀昊天上帝禮)並付諸行動,全錄鄭注。不過在幾個涉及祭禮最核心的理論問題上,他對鄭注也進行了徹底的批判。如對鄭玄以讖緯解天神、地示祭禮的批評;又如鄭玄的禘祫理論一出,對歷代的學者影響甚鉅,信服者甚眾,楊復卻以洋洋灑灑近三千言(卷八中,),對鄭玄禘祫志作糾謬的工作。元人趙汸云「向來嘗感楊信齋譏鄭玄讀祭法不熟,……罔乎後世而傲視古人如此」(答徐大年書,東山存稿,卷三),今人錢玄則表示楊復評斷鄭玄「以無為有,駕虛為實」,是「確切而銳利」的評價。(三禮通論制度編。楊復所論,乃錢書轉引自黃以周禮書通故。)且不論楊復立論是否妥當,更值得注意的是,楊復首先在通禮篇確定祭禮整體理論,然後根據這套理論去編輯卷四以下的具體内容。上文已見他在卷四、卷五的引文中刪除有關周公攝政的字詞,是一個淺顯的例子。理論原則貫通全編,至於引文的細節都要受理論原則控制,進行刪節調整,這是朱熹經傳通解、黃榦通解續未曾出現的情況。
楊復又廣納宋人經說,除朱熹以外,又有程頤、孫奭、司馬光、陳祥道、李如圭、陳孔碩、黃度等人,充分呈現出宋人對歷代聚訟的古今儀法制度問題的看法,並且根據自己事先樹立的理論原則評論是非。最特殊的是他在說解禮儀時,引用前朝或當朝詔令奏議的內容,而評斷態度一仍前所述。唯有透過朝臣在朝廷中對經書與禮制的討論過程,才能證明禮儀真正的實行情況,而不再只是紙上談兵。楊復從禮學理論的角度對各種禮議進行評斷,使朝廷議禮與經學家的學説並列,納入到同一個禮學理論的框架内,可以説是經學統攝禮制的特例,亦是編纂禮書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三)隱藏已久的一條禮學脈絡
禮學介於經學與歷史、理論與實踐之間,包含多方面複雜的内容,而宋、元、明、清四朝的每一位學者選擇的重點與視角都不同。以往,我們不知道有楊復的祭禮,因此對朱熹的禮學似懂非懂;以往,我們不知道文獻通考深藏著有關朱熹一門的禮學理論,因此總以為清代禮學家跨過明、元,僅僅是遠紹朱熹的禮書編纂方式而已。現在因為楊復祭禮的重新發現,我們能夠在朱熹、黃榦、馬端臨之間,再加上楊復,進行對照。在他們之間,除了直接的承襲因素之外,更突顯出各自不同的鮮明特質。我們因此對朱熹、黃榦、馬端臨也能得到新的認識,進而勾勒出一條隱藏已久的禮學脈絡。
在楊復祭禮之前,如唐開元禮者,雖通事舍人王嵒曾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學士張説以「禮記乃不刋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為由作罷,最後是以折衷唐貞觀禮、顯慶禮,分吉、賓、嘉、軍、凶五禮,而為開元禮(新唐書禮樂志,卷十一),經學迷失而成禮制儀典。自此往下,太常因革禮、政和五禮新儀、大金集禮等皆一朝儀典,同屬一類,在本質上與經學不同。
又如唐通典者,雖「採五經羣史,每事以類相從,舉其終始,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羣士論議得失,靡不條載,附之於事」(通典序,李翰),乍看之下似乎與楊復的做法沒有差別,實際上正好相反。通典是史書,雜糅各種資料,編成一部制度史,每一類制度按時代編排材料,周禮、儀禮只當作周代的歷史記載,與其他各代資料並列,經書無獨立地位,勉強可以說是經寓於史。
朱熹開始纂修經傳通解,重點在經學資料的梳理,而酌錄少數歷代議論,又另撰家禮。家禮是書儀之流,本不屬經學,繼司馬光、二程之後,至朱熹始多經學理論之考慮。但經學與禮議、經學與禮俗,語境不同,各有不同的考慮,始終未能渾然一體。
楊復爲經傳通解補撰祭禮,立足明確的經學理論,網羅匯聚經傳資料,連歷代禮制、奏議也在同一經學理論的平臺上討論是非,是史寓於經。楊復另撰儀禮圖、家禮注,努力使家禮盡量接近儀禮。儀禮圖、家禮注與祭禮三部著作,形成一個共同的體系,互相之間有重疊而無矛盾。朱熹所關心的經學、禮議、禮俗等不同方向,可以說在楊復的調和下達到了一種統一。
在楊復祭禮之後,出現了一部對傳播朱熹一派禮學非常重要的著作──文獻通考。楊復的禮學理論被慧眼獨具的馬端臨認同,因此文獻通考有關「祭禮」的部分,即全面採用楊復整理的理論體系,他在自序中說:
蓋古者郊與明堂之祀,祭天而已。秦漢始有五帝、太一之祠,而以古者郊祀明堂之禮禮之,蓋出於方士不經之說。而鄭注禮經,二祭曰天、曰帝,或以為靈威仰,或以為耀靈寶,襲方士緯書之荒誕而不知其非。夫禮,莫先於祭;祭,莫重於天。而天之名義且乖異如此,則其他節目注釋雖復博贍,不知其果得禮經之意否乎?……至於禘祫之節、宗祧之數、禮經之明文無所稽據,而注家之聚訟莫適折衷,其叢雜牴牾,與郊祀之說無以異也。近世三山信齋楊氏得考亭、勉齋之遺文奧義,著為祭禮一書,詞義正大,考訂精核,足為千載不刊之典。然其所述一本經文,不復以注疏之說攙補,故經之所不及者,則闊略不接續。杜氏通典之書有祭禮,則參用經註之文,兩存王、鄭之說,雖通暢易曉,而不如楊氏之純正。今並錄其說。
儀禮圖
文獻通考是一部關於研究上古至南宋嘉定末年各朝代典章制度的史書,從元至清,文人士子必讀,其影響甚鉅。雖然,馬端臨以史書的體裁要收錄楊復祭禮的內容,造成他編撰上的困擾,但他終究對「千載不刊之典」無法捨棄,只好割裂楊復全書,依據類別,而分置各個儀典之下;而且在每個儀典之下,先錄經傳註疏以及楊復等人的理論敍述,後列歷代禮制以及禮議、奏議等資料。馬端臨分開經學與歷史,先經學,後歷史,儘管出於史學家對朱熹一門經學的尊崇,實際上也意味著經學與歷史的再度脫節,承認歷朝的禮議不適合用經學理論的框架來判定是非。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楊復祭禮將經學理論的地位提升到空前絕後的高度,一切事宜都要用經學理論來審定是非,具有突出的典型意義。
明清兩代的禮學家們幾乎都是透過文獻通考來理解楊復、亦即是朱熹的祭禮理論;或者如秦蕙田的五禮通考、黃以周的禮書通故,都間接地從文獻通考中引用楊復祭禮的觀點作為自己解經的根據。換句話說,朱熹一派完整的禮學思想,除了經傳通解外,是透過文獻通考對後代禮學家產生潛移默化的巨大影響。可是,在看不到楊復祭禮原書的前提下,沒人能想像楊復祭禮與文獻通考之間存在編纂體式的根本性差別,兩者指向的方向幾乎完全相反。
現在我們看到楊復祭禮的内容,才看到楊復祭禮將朱熹一門的祭禮理論思想發揮到極致,也了解到馬端臨以史學家的眼光對楊復祭禮進行徹底改造,具有重要的創新意義。禮學包含經傳、經學理論、禮議、禮俗等複雜因素,每一學者重點不同,形成不同的編纂體式。從這一角度來看,開元禮、通典、朱熹通解、楊復祭禮、文獻通考這五部著作的體式特點,都格外鮮明,可以說這五部具有典型意義。再往後看,秦惠田五禮通考採用的就是文獻通考的體式,是馬端臨的嫡系。至於黃以周禮書通故則是經學理論的疑難考辨集,自然不得與五禮通考等同歸一類。
總之,這部書的整理出版,解決了朱子禮學文獻缺乏的問題,是澄清朱熹禮學思想來龍去脈最重要的一部宋代文獻,定會使朱熹禮學的研究推進到從未有過的深度。朱熹曾說「楊志仁有過於密之病」,言下之意,覺得楊復治學過於謹慎小心。如今看來,若非楊復之「過密」,就不會有祭禮這部思想嚴謹周慮的著作,朱熹的禮學思想也無法重現於世人面前。而楊復祭禮在禮學史上的重要性,更自不待言了。筆者識見有限,相信讀者們細細品味此書,將有數不盡、論不完的發現。
注释:
[1]論述全面且較具影響力的早期研究成果,在中國大陸有白壽彝先生的儀禮經傳通解考證(北平研究院院務匯報,7卷4期,年);在臺灣有戴君仁先生的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與修門人及修書年歲考、書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後(梅園論學集,年,臺灣開明書店);在日本有上山春平先生的朱子の禮學──儀禮經傳通解研究序說(人文學報[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第41號,年)與戶川芳郎先生的和刻本儀禮經傳通解解題(和刻本儀禮經傳通解,年,東京汲古書院)。
[2]近來的學者已有此意識,認為朱子的禮學還是應該回歸到儀禮經傳通解的文本上探討,如有張經科先生儀禮經傳通解之家禮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年,董金裕指導),逐章分析儀禮經傳通解中家禮的內容;孫致文先生朱熹儀禮經傳通解研究(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年,岑溢成指導),從文獻學、經學詮釋學等角度分析儀禮經傳通解,並說明此書的現實意義與學術史上的意義。其他朱子禮學相關研究,請參考林慶彰先生編經學研究論著目錄與朱子學研究書目(-)。
[3]如孫先生朱熹儀禮經傳通解研究稱:「儀禮經傳通解續喪禮、祭禮部分,因為都未經朱子審定,因此不列入本研究討論範圍」。
[4]答黃直卿七中,朱熹針對喪禮內容與黃榦斟酌篇目與內容之編排,見晦庵集卷四十六。
[5]呂氏寶誥堂所刊之儀禮經傳通解,封面有木記稱「禦兒呂氏寳誥堂/重刻白鹿洞原本」,而其中所收祭禮為黃榦祭禮,並且具有元統間余謙等重編喪、祭禮通訂目錄。然嘉定刻本後歸國子監,余謙等在西湖書院進行修補,後其版當在明代國子監,何得稱「白鹿洞原本」?此可疑之處一也;又,靜嘉堂文庫所藏楊復祭禮有「南陽講習堂」之刻印,「南陽講習堂」即呂留良之所,說明呂氏亦曾擁有此書,但呂氏寶誥堂刊儀禮經傳通解時,未使用楊復此本。此可疑之處二也。
[6]原刊於東方學報(東京),年2月。今由刁小龍先生翻譯,刊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0卷第2期,年6月。
[7]下引朱熹文集及語錄,均見朱子新學案,不另作説明。
编辑:沛原
全国最好的白癜风医院头部白癜风用什么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