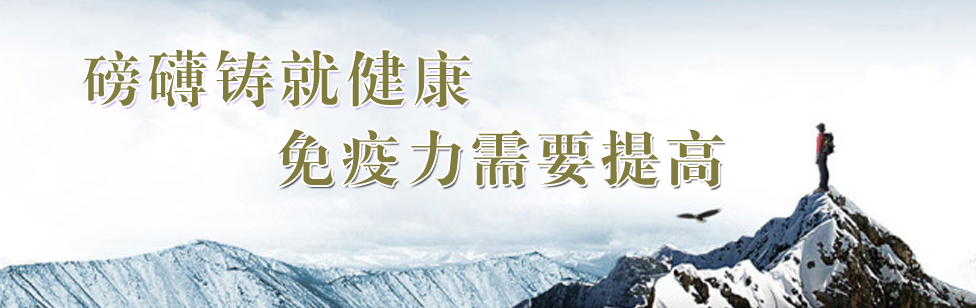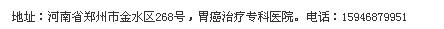医学是不是一种文化?我的理解是:文化是人类包罗万象的感受和行为,她无关乎优劣、雅俗和高下,只是认同感有异。医学也应该是一种文化,靠文化承传,靠文化立命。
医生如果不谙熟中国文化,有时为病人提供的是他并不需要的医学服务,或不能理解病人的心灵向往。尊重患者的自觉需求是医学的信仰文化。
医学承载着感恩文化几天前一位紧张兮兮的女白领前来就诊。一番诊断后,告知她所患甲亢为桥本氏病而非格雷氏病,嘱其不必紧张。交谈中她饶有兴趣地问起这两个病名的来历。我解释道:“以发现或总结某个疾病的医生名字命名病名,是西医的一个惯例。其相应的中文病名是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合并暂时性甲状腺机能亢进和弥漫性甲状腺肿伴甲状腺机能亢进症。”说起来冗长拗口,显然没有桥本病和格雷病易记。每次在描述该病时,我便对伟大的日本Hashimoto医生和爱尔兰RobertJamesGraves医生产生一次缅怀和感激。诸如此类以发现或发明者命名,已成为尊重前人的世界文化。在上世纪60年代那场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运动中,这一世界文化也被洗劫。其实临床医学是一代代先贤聪明才智的积累,是依靠著书立说或言传身教传承下来的技艺。只有感恩先师和前辈,医学才得以生存和发展。
医学行使着仪式文化 广州中医药大学的一位著名教授,每逢出诊必沐浴更衣,梳理装扮。她身上体现了医生临诊病人前的职业神圣感。我长期行医也养成了一些习惯,仪式感极强,否则临床思路就变成真空。也有一些医生不注重仪式,甚至连必要的诊疗程序也视同儿戏。如医院,三天后惶恐地打“明天上午就要做心导管了,怎么还没有一位医生听过我的心脏?”其实住院三天,医生为她做了一系列详细的辅助检查,并与家属沟通好要做PTCA。虽然事后证明管床医生导管技术娴熟,治疗效果也不错,但在诊疗过程中居然没用听诊器听诊心脏。且不说缺失基本医学操作的规范性和病历采集的真实性,至少让病人没有经历医生亲临床边这个不可或缺的仪式。其实医学的前身曾是巫术——一种仪式感很强的降神和咒语过程,充满了神秘感和震慑力。现代医学已经借助太多的“火眼金睛”直达生命要害,摈弃了许多“虚假”仪式。但是作为一种维系生命和灵魂的职业,除了必要的医学程序外,带有神圣感的仪式也绝不可形同虚设:查房的站姿、望诊的眼神、问诊的语气、听诊的神情、叩诊的手法、病历的格式等等。在这些仪式行使过程中,除了收集到必要的医学信息外,也展示着医生对生命的尊重和病人的关爱。仪式是安抚病人情绪的魔杖,必要的行医仪式树立的是医生的威信。
医学体现着信仰文化有位亲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笃信一种“特效”治疗,而这种疗法每每带给她神奇疗效,她也乐此不疲地向周围朋友推荐。起初自认受过正规训练的我,每每不屑于她那无厘头的偏方,也多无视她叙述的确切疗效。随着临床资历的增长,逐渐理解了“信则灵”背后的医学关联和人文力量——心之所向,神之所往。我们所谓经过严格训练的医生,不也是在滔滔不绝地向病人“兜售”我们笃信的科学方法吗?而其中一些科学方法后来又被循证医学或事实证明是错误的。比如,早年提出定时定量科学喂养婴儿,最后返璞归真为即时母乳喂养;更年期雌激素普遍应用、糖尿病要忌糖和甲亢要忌碘等,也都曾被医生们坚定地执行。所谓科学合理的治疗措施,往往在那些未被说服的病人身上无法奏效。任何疗法都有1/3的心理暗示作用,心灵向往有时可以改变一些疾病的转归。长期以来,对病人心理向往的忽略和对病人社会属性的无视,自认为正统的医生并未意识到这有何不妥。现代医学前一只脚刚踏出了半巫半医的丛林,后一只脚又陷入技术迷信的泥潭。迷信和信仰可能是不同话语体系的共同体。对于心理停留在迷信层面的病人,应当变换思维方式尊重他们,鄙视病人的无知或许是医生的无知。对于只停留在技术层面的医生,也要启蒙他们的人文修养,过度依赖技术其实就是一种迷信。因为文化浅薄,只看问题表面;因为文化沙漠,处理事情急躁。没有文化的医疗技术是生硬、冰冷和乏味的重复。至少我也是该类“病人”之一,也需寻医问药,或许该自我疗伤。
医学需要文化力量的引导
医学在现代社会是一个很容易被误解且经常被低估的领域。早些年,医务人员被认为是单纯的专业技术人员,是“臭知识分子”,虽然有些专长,但脾气性格古怪,言行常常让人难以理解,也被某些所谓“高贵”的人认为也不就是伺候人的人吗?随着经济全球化,医疗市场也随整个社会步入市场经济,当“非典”“地震”等大灾难来临时,医务人员毫不犹豫地冲锋在前时,他们被全国人民称之为“世界上最可爱的人”,可是在风暴过后的平静日子里,医务人员的“白衣天使”形象就被不良媒体炒作成“白衣狼”,虽然真正有这种看法的人是极少数极端偏执的人。大多数人认为医务人员是专业技术性很强的吃技术饭的,但没有多少人认为医学是个文化?量很高的行业。医学文化对于普通人来说很新鲜,以至于有人认为把医学与文化关联起来是否有些牵强。 其实追溯其渊源,医学本身不但离不开文化,而且是以文化的形式存在的,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代中,医学都因文化而更温馨、更可靠和安全、更加有人文关怀、更有发展前景。《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文化建设既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目标。”美国学者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也曾说,“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医学的发展历史也已经证明:对医学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资金。 历史不会忘记,当年青海与西藏解放时,解放军进驻青藏高原初期,众多少数民族群众因文化、习俗、语言、信仰等与汉族部队官兵的差异,对国家政策并不理解,在开展社会各项工作时是有很大困难的。这时医学文化的力量就显示出来了,医务人员带来先进的医学技术和仁爱的理念为各民族群众防病治病,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从先进的医学技术和医学文化对普通少数民族群众的关爱中,让广大民众逐步了解和理解新政权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扶持政策,最终新生的人民政府获得了各族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人们更不会忘记,每当大的灾难来临,医务人员总是先人后己和大爱无疆地冲在最前沿,为广大民众防病治病。无论是“非典”肆虐,还是四川、玉树大地震,医务人员在第一时间不顾自身危险全身心地投入灾难现场,为政府分忧解难,为社会稳定赢得民心。这些无不彰显医学文化的巨大作用。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医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集政治影响力、社会亲和力、民族凝聚力、民生感召力、文化传播力于一体,是我国多民族文化共识和社会和谐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而另一方面,医学需要文化,医学没有文化的牵引就只能是生物学的单纯技术。医学文化是人类长期医学社会实践的产物,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医学领域中通过物质因素、精神因素、规制因素、行为因素和心理因素承载的人类关于医学的所有主观信息,是指导人们进一步进行医学社会实践的原动力。发展医学文化,不仅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各民族群众的需求,是我国医疗体制改革走向成功的必然选择。 很多人以为医学就是医疗技术,医务人员就是单纯的专业技术人员,其实这是生物医学模式陈旧的技术观念。医学包括了理念、态度、思维体系、科学技术、社会人文等多个方面,是基于人的健康、生死等众多问题而对万事万物相知和文化的融合。因此,我们说人类社会问题涉及的范围有多广,医学文化的范围就有多广;人类文化体系有多大,医学文化体系便有多大。医务人员和医疗行政管理者从事医学文化的拓展,并非“不务正业”,而是集人类对医学问题的认识、理解之大成而建立的医学文化,不仅博及物与理、兼容道与元,并在整个社会领域之中庞而不乱、博而不庸、纲目清爽、条缕明晰,虽纵横捭阖于术理,然据宗守本成体系。因此,医学是以自然科学为基?内核,兼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思维科学而形成的高度复合知识体系。所以,医学文化是社会意义鲜明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和人文科学熔炼出来的多元文化。 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和医疗设备设施都已与世界接轨,医学技术水平已不亚于发达国家水平,换句话说,我国就医群体已经享受到了世界最高水平的医疗技术,有的医学科学成果也走到了世界的前列。但必须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医疗保障体系和经济水平尚与世界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医院的科学管理方法和理念上以及医疗卫生队伍的整体素质上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巨大,难以与世界接轨。例如我国医疗机构通过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的世界最先进的医疗质量管理体系——美国医疗机构评定国际委员会的认证(JCI认证)很少,在医疗制度与规范、医疗行业管理、医疗安全与患者满意程度、医院运营与服务理念及人员素质等医学文化发展上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医院医院文化建设,但我国在医学文化层面的发展并没有使广大就医群体满意,与世界接轨的医疗设备及医学科技水平也并不相符。 的确,我国有博大精深的民族医学文化,有深厚的民族医药历史文化,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现代生物医学科技队伍,有世界上最多的医疗机构,也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医疗保障人群,但对于一个真正的医学文化大国来说,这些似乎还远远不够。换句话说,由于我国医学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并不相适应,我国的医疗体制改革任重而道远。医学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氛围仍不够深厚,民众对“医改”的进程和效果并不满意,人民群众对医学文化的认识还有待深化。我国医学文化的特色依然不够鲜明,医疗安全文化和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尚未真正与国际接轨,医患矛盾依然突出。 医学文化建设虽然是一个漫长的积淀过程,但首先要转变观念,认识到医学文化是各民族文化共识的重要性,以医学文化的“教化功能”对社会成员文化共识和民族认同感的认知与观念进行引导和强化,从而在提高全民族健康水平和整体素质的同时,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医学文化的深厚博大共同凝聚中华民族的牢固精神纽带,不断促进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文化力量。
王岳:感悟医学人文
十几年前,当我站在人生择业的十字口。我“任性”地选择了自己喜欢做的事——到北大当老师。我喜欢大学的氛围和孩子们天真的笑容,更喜欢大学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此时的我已经懂得,选择职业就是在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年在韩启德院士的倡议下,北京大学医学部成立医学人文研究院,而我有幸成为这所年轻学院中的一员。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化,也让患者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最典型的标志是患者权利意识的觉醒和膨胀。这就要求医学生必须清晰地洞察这一变化,并感悟和认同医乃“仁术”,更是“人术”。但是,中国的医学教育仍停留在生物医学模式的教育中,人文社会科学在医学院的教育中一直被边缘化,医学生被培养成了“有知识,没文化”的技工,而伴随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进步,步入临床的医学生愈发感觉力不从心。北京大学医学部率先对医学教育改革进行了尝试,开始设立加强医学生预科教育的医学人文研究院,设立医学伦理与法律研究中心,加强对医学生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教育。能够作为一所学术机构成立的最早参与者,对我们年轻教师来说,这无疑是最大的幸运。“医学人文”是一种感悟实际上,医患关系日趋紧张,除了制度等因素导致,也反映出医学模式亟待转型是一个既重要又漫长的工作。振奋之余,我感到的更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医学人文”不是知识,无法讲授;“医学人文”不是能力,无法锻炼。而我越发感觉“医学人文”是一种感悟,是一种心灵深处的共鸣,一种内心世界与人文精神趋同的价值观。而医学人文教育应是让学生在授课过程中逐步去感悟和最终形成这种价值观,因为这才是一名医生必备的素质,也是医生“永不被告”之关键。我常提醒自己,尽管从事法学教育工作,但必须让学生感悟法律所体现出的人文关怀。我常害怕,今天已经处于惊弓之鸟的医学生,会被社会目前颇为主流的价值观和高深莫测的法律知识引入歧途。给医学生补上一节人文课东方人长期处在封建专制文化的压榨下,人们的自由、正义观相对贫乏,尤其在法治层面理解正义的内涵时显得较为迟钝。所以我们要给医学生补课,补上以人为本、以患者权利为中心的一课。首先,应当让医学生知道医与患利益统一。因为今天的医生明天也会成为患者,今天我们用什么样的规则、态度对待患者,明天迎接我们父母、子女和本人的同行就会遵循怎样的规则和态度。其次,应当让医学生明白医患法律关系维系的基石便是信任。如果你多花些时间去安慰、聆听、帮助患者,你就一定会得到他的信任,你们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就稳固了。第三,应当让医学生了解患者的权利,如果说人的生物属性体现于每个细胞,则人的社会属性体现在每项权利。只要你遵守了患者的每项权利,你的执业就是安全的。第四,应当让医学生了解执业者的注意义务,了解为什么美国人称之为“小心的责任”,日本学者称之为“良父义务”。因为执业者经过训练就要比患者在临床安全方面更有“预见力”,而预见到“风险”之后执业者经过训练就要懂得,我必须首先“告知”他,其次我要比患者更有办法,立即采取措施避免“风险”发生,或降低“风险”发生的几率。作为医学院的法学教员,我希望通过有效的学时对医学生进行法学教育,让他们了解法律、感悟法律、崇尚法律,理解法律不是文字和条款,领会法律背后彰显的人文关怀和价值取向。同时,我也积极投身于在职医务人员的医学人文培训工作中,因为我相信他们会从我们的课程中获得受益。
北京最好的白癜风医院在哪里沈阳最好的白癜风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