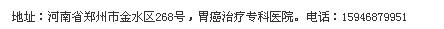点击蓝字学衡,添加19年以来最为坚守的人文学科垂直媒体与服务平台
文化危机与知识应对:从胡先骕的知识结构看《学衡》的文化保守主义王刚
胡先骕先生是“中国植物学之父”,作为一位现代科学家,在人文领域,他却以文化保守派的面目出现。0世纪0年代,作为《学衡》主将之一,与文化激进主义展开了激烈的论战。知识分子之间的交锋,从本质上来说应是价值之争,它必须依托知识而展开,这也就决定了论战者文化背景及知识结构的重要性。在学衡派学人中,胡先骕拥有他人难于取代的知识结构,理由至少有二:一是他留学美国,最终成为自然科学的巨子,但并不媚外,一生服膺中国传统文化,古诗文造诣深厚。二是他以科学家身份兼作文学,成为文学论争中的核心人物,在中国近代学术界称得上绝无仅有。在那个以科学和西学为荣的时代,这种知识结构具有极大的文化威慑力,从而也给《学衡》的创立和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下面,我们就以胡先骕的知识结构为考察点,去看看在近代知识转型背景下的学衡派及文化保守主义。
一、知识转型与知识人的结构调整:晚清到民国的士裂变
近代中国是一个大裂变的时代,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结构的剧烈转型中,更体现在对思想文化造成的冲击上。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其最大震荡其实还是文化上的,一个思想统一的大帝国突然间失去了精神方向后,迷茫失措,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大危机。不变化就没有出路,变是唯一的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学习西方成为了必然的选择。于是近代中国开始由妄自尊大走向学习西方,变与学日渐成为思想的主旋律,然而,怎么变、如何变?这个问题在思想界一直得不到统一的认识。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改变过程中,对于传统是有所保留还是全盘抛弃?与之对应的是,对西学的态度,是中体西用还是全盘西化?这是一个严肃的选择。于是,在近代中国,守护还是抛弃的矛盾就显得异常突出,而所谓文化保守主义也由此而起。
文化的守护和抛弃不是简单的器物置换,这种变动必将带来一连串的震荡和反应,其艰难与复杂异乎寻常。而这其中最重要的结构性变化,莫过于古典知识的扬弃及知识群体的裂变。从社会传统来看,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化大国,从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是个以文化立国的民族。作为文化传承最重要的力量——士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中心位置,他们以文化所带来的优越性而取得社会支配权。所谓“学而优则仕”,使得传统中国文质彬彬,士大夫亦学亦官,文化自豪感一直维系了数千年。马克斯·韦伯(MaxWbr)曾指出:“(在传统中国)由教育特别是考试规定的出仕资格,远比财产重要,决定着人的社会等第。”[①]毫无疑问,士阶层地位的形成是历史的过程,但是其基本内核却一直是知识系统,这种知识不完全同于西方,具有神圣性与强制力。所谓学统、道统、政统中,士大夫一直以自己的知识体系傲视王侯,拥有“学”的正当性是其他一切的基础。具体来说,这种知识体系以儒学经典为核心,是传统士人安身立命的关键所在,也是前近代士大夫的价值基础所在,如果失去了它,士大夫就没有了身份依托。然而,时至近代,这种知识系统一步步地遭到了否定,它对于士大夫的解体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与此同时,随着知识基础的转移,新式的知识分子开始产生,他们的知识基础或者说立说依据不再是古典知识,而是所谓的现代西学,知识权威或文化资格发生了重大位移。从科场到学堂,从中学到西学,不仅是知识基地的转换,更是知识分子结构的巨大调整。
但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进化论或新陈代谢的眼光,来看待知识文化的变迁,士人的逐渐消失及被排斥,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的彻底死亡。除了死守传统的遗老遗少,一批要求保存旧文化的新人物日渐出现,以学衡派为代表的新文化保守主义者就是其中的典型。这些现代中国的保守主义者并没有复古癖,相反的是,他们大多具有良好的现代眼光及知识背景,与文化激进主义者全盘抛弃传统不同的是,他们要做的是旧学的现代转换。这种转换主要是在东西文化调和的基础上,以西学为基础进行中学改造,以造就一种新的文化,《学衡》简章中说:“期以吾国文字,表西来思想。”这就与新文化运动前的保守主义有了很大的不同。有专家指出:“在文化学的理论方面,学衡派与当时其他文化保守主义流派多直接取资于儒家传统价值观念的做法不同,而是试图按照西方新人文主义的学术途径,去从事未来文化框架的设计和建设,由此形成了其鲜明的个性。”[②]我们或者可以说,在文化危机面前,激进和保守两种路向,是出于两种不同的价值观而产生的知识应对,它们都植根于现代知识及价值体系上,而非所谓的倒退与进步的对立。在救国与启蒙的双重任务中,知识分子们希望以西方资源来造就一个新的中国,于是中国问题后面大多有了西方的思想背景。但他们所面对的西方并非铁板一块,随着理解的深入,西方的思想文化日渐呈现出各种面相,中国知识分子也面临着多元选择。一时间,各种西方思潮纷纷登场,知识分子按照各自喜好与背景加以不同的选择,各种思想及学术流派相互碰撞,争雄一时,从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从士大夫转换为近代知识分子的那一刻起,这一阶层就已经由同质性转为异质性的群体,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产生之初就是碎片化的,这种碎片就溯源于不同的思想路线之中。文化价值的差异使得他们从一开始就分裂、游弋在不同阵营,而这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激进与保守主义的对立。
按照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在知识分子阶层中,价值及知识分歧是极为重要的分野,并由此产生不同的文化阵营,文化论战的激烈程度也往往与分歧的大小成正比。所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LwisCosr)将知识分子称之为理念人(mnofidas)。换言之,知识分子就是生产及捍卫理念的人,并由此产生剧烈的论争,近代中国之所以文化论战异常激烈,正反映着背后理念价值、知识系统的剧烈差异。
二、“西与西斗”中的胡先骕:留学背景与话语权问题
士人裂变为近代知识分子后,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知识群体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话语权的争夺过程中,文化论战出现了,而这其中最大的对立阵营则是文化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文化激进主义者多具留学背景,一直以来以西学相标榜,颇得时人信从,在这种新知识体系面前,旧式士大夫纷纷败下阵来,与《新青年》为敌的古文大师林纾等人最为典型。然而,0世纪0年代学衡派的出现改变了这种不平衡的格局,在知识对等性上给文化激进主义造成了巨大的阻力。
学衡派的崛起与其留学生背景有重大关系。众所周知,《学衡》杂志于19年1月在南京东南大学创立,它和文化激进派相抗衡,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坚固营垒,学衡派名号亦由此而起。杂志的具体发起人为梅光迪、吴宓、胡先骕、刘伯明、柳诒徴、萧纯锦、徐则陵、马承堃和邵祖平等九人,其中前五人最为重要,有学者称其为“《学衡》杂志的五大主力人物。”[③]这五人中,除柳诒徴外,都是留学生身份,一比四的比例足以说明,作为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学衡》,对于传统文化及本土学者的重视固然为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其大部分骨干却是来自西方,西学色彩,简言之,留学生色彩之浓厚,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当以留学生为主力的学衡派与文化激进主义展开论战时,已不再是过去那种意义上的新旧之争,比之陈独秀、胡适等人,学衡派诸子的西学色彩有过之而无不及。罗志田说:“《学衡》杂志的出现确有象征性的转折意义。……到19年《学衡》出,表面上似仍以对中国传统的态度区分,实际上已成为西与西斗,争的是西学正统。”[④]这种所谓的“西与西斗”,其实质是要打破激进主义者对西方文化资源的独断。与以前的保守派着眼于赞扬古代,排斥西方不同的是,学衡派也是宣扬西学的一支重要力量,西学同样是他们的知识基础。所以梅光迪曾说胡适等人是“伪欧化”,“以彼等而输入欧化,亦厚诬欧化矣。”[⑤]抛开意气之见,以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这是一种对西学话语权的争夺。
比之学衡同仁,胡先骕在这方面的意识更为强烈,所以冲击力也更大。胡先骕虽是农科出身,但人文修养十分深厚,在中学方面,他先后受业于沈曾植、林纾,问学于陈三立,这些人都是旧学中的宗师或翘楚,所以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曾以“吾友胡先骕”的词作为“陈词滥调”的代表加以攻击,以期敲山震虎,进而吹起新文学运动的号角。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胡先骕对文化激进主义的论战,是因其新学中的旧色彩而被迫卷入的,这一点与其他学衡诸子很不一样。[⑥]在西方人文理论方面,胡先骕也十分熟稔,故常能以严密的科学眼光,运用西方资源对激进主义展开论战。他思路敏捷,写作速度快,吴宓在评价《学衡》诸人时曾说:“(胡先骕)直爽活泼,喜多发言,作文迅速,为当时《学衡》杂志最热心而出力最多之人。”[⑦]
当时激进主义的文学阵营也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比之此前被他们击败的古文大师林纾等人,郑振铎曾指出:“林琴南们对于新文学的攻击,是纯然出于卫道的热忱,是站在传统的立场来说话的,但胡梅辈却站在‘古典派’的立场来说话的,他们引致了好些西洋的文艺理论来做护身符。”[⑧]这其中所说的“胡梅”即指胡先骕与梅光迪,在《学衡》初期,在文化激进主义者看来,他们是最为重要的论敌,而他们的武器则是“西洋的文艺理论”。[⑨]我们可以这么说,当激进主义者揣着舶来的傲慢,将传统文化视之为腐朽、妖孽的代名词时,以胡先骕为代表的留学生群体正是凭着入室操戈的手段,用西方理论武器来捍卫传统的价值及尊严,虽声音还稍显微弱,但却拥有强劲的战斗力。所以,当时属激进主义文学阵营的陈子展就曾说:“胡先骕这可以说是文学革命者自林纾而外所遇的又一劲敌。”[⑩]
在留学生之间的抗衡中,胡先骕还特别强调留学生守护传统的责任,以与激进派分庭抗礼。19年他在一篇《说今日教育之危机》的文章中论述道:
吾尝细思吾国二十年前文化蜕变之陈迹,而得一极不欲承认之结论:则西方文化之在吾国,以吾欧美留学生之力始克成立,而教育危机亦以吾欧美留学生之力而日增。吾国文化今日之濒于破产,惟吾欧美留学生为能致之,而旧文化与国民性之保存,使吾国不至于精神破产之责,亦惟吾欧美留学生为能任之也。[11]
从上文我们可以了解到,胡先骕认为,在西潮冲击之下,作为引领风潮的留学生群体具有挽救本土文化危亡的责任。在西学的强势面前,留学生以其知识优势,既可以使得传统破产,同时也能借助西学之力,保存固有文化。具有文化责任感的留学生应成为挽大厦于将倾的群体,承担起传播西学和守护中学的双重文化任务,这是他们新的文化使命。在胡先骕及学衡派那里,西学不再成为摧毁传统的力量,而是使传统得以自存发展的知识屏障。这样一来,它就呈现出了全新的面貌,成为了传统文化得以不间断地走向未来的转换器。这是立足于现代文化发展之上的推论,是对中西学术文化的一次重大调整。概言之,传统是断裂还是得以保存,已主要决定于西学的运用及留学生的态度,争夺西学话语权及留学生中的主流地位,基础在于西学,落脚点却是在中学之上,为了文化传统的保存,这种争夺已成为势在必行。当西学话语权完全掌控于激进主义者之手时,传统被树为西学的对立面,贬得不名一文,甚至被极端妖魔化,现在随着这批欧美留学生的出现,中西学关系终于得到了转换,一边倒的格局开始改变。如胡先骕曾讽刺钱玄同“中国旧学者也,舍旧学外不通西学者也,乃言中国学术毫无价值。”[1]倘非具有留学背景的同道中人,是不敢下此断言的,且前引文中一再言道“欧美留学生”云云,隐然有对陈独秀等速成型,且不正宗的东洋留学者的轻视。而这些人在文化激进主义者中占了极大部分,在这种特殊语境中,胡先骕的态度就不是单纯对其身份的轻视了,而是话语权的一种另类争夺。[13]总之,他利用自己的知识优势,反复强调激进主义者对于西方学术的隔阂及误读,其目的在于为自己争取理论制高点,以赢得人们的理解与同情。
三、“理致”与“时代”:新文学视野下的旧诗文与新学术
《学衡》并不只是留学生的天下,对于本土文化的强调,使得它与旧学血脉相连、不可分割。但创办之初的《学衡》在旧学上也的确存在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作为创办主力的留学生群体,他们的旧学修养在当时有所缺憾。二是《学衡》在理论上是以西学为指导,旧学人士虽也参与其中,但主要是发表旧体诗文,无力运用西方理论开展文学研究及批评。三是当时与文化激进主义的论战点主要在白话文尤其是白话诗方面,胡适自己曾说:“新文学是从新诗开始的。最初,新文学的问题算是新诗的问题,也就是诗的文字的问题,哪一种文字配写诗?哪一种文字不配写诗?”[14]而这就需要具备诗歌创作实践者参与其中。要解决这些矛盾,必须要有一个精通西学理论,又兼通古诗文之人,胡先骕就是这样一个人。
当然,学衡派中如吴宓、梅光迪等留学生也通晓古诗文,[15]但是他们的诗文训练,及与旧学人士的密切度显然不如胡先骕。前已提及,胡氏早年师从沈曾植,沈为当时顶级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曾推崇道:“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于名一家,立一说。”[16]胡先骕的兴趣在古诗文,尤好“同光体”,而沈又是当时“同光体之魁杰”[17]。源于以上关系,青年时期的胡先骕对于古典诗文的情感及修养远在一般学人之上,这成为他与旧文人及热爱古诗文者最重要的文化纽带。这种纽带主要作用于两类人群,一是传统学者;二是没有留学背景的《学衡》同仁。前者如张鹏一、周岸登、王瀣;后者主要有邵祖平、马承堃、王易、王浩等。
总之,胡先骕的学术素养使他足以承担弘扬古诗文的重任,他也由此成为新文学运动中,反对以白话诗替代古诗的最大主力。长期以来,他及学衡派被认为是阻扰新文学及新诗发展的反动力量,但这不过是一种二元对立思维的简单推想。学衡派并不反对新文化,梅光迪曾说:“夫建设新文化之必要,孰不知之?”[18]从学衡派的知识背景来看,他们大多留学海外,浸润于西学,怎么可能无端地反对新文化或新文学呢?这个问题的提出本就是历史的误会,甚至就是歪曲武断之言。《学衡》从来不反对新文化,反对的是毁弃古文,消灭古典的新文化。或者说,不赞成当时的那种激进方式。
就胡先骕及他的古诗文来说同样如此,他做古诗文不是为了故意反对新文学,而是希望有更为稳妥的文学改良之路。他曾表白道:“素怀改良文學之志,且与胡适之君之意見,多所符合。独不敢为鲁莽灭裂之举,而以白話推倒文言耳。”他还进一步指出:“彼故作堆砌艰涩之文者,固以艰深以文其浅陋,而此等文學革命家,則以浅陋以文其浅陋,均一失也。而前者尚有先哲之规模,非后者毫无文學之价值者所可比焉。”[19]在胡先骕及学衡派看来,在新诗的创立发展过程中,如果按照胡适等人的主张,去掉一切束缚,诗没有了规范,那就失去了诗的韵味,走入了绝路,以白话推翻古文,以俗替代雅是一种极端之举,属于“以浅陋以文其浅陋”。简言之,文学的改良不应是从文字形式上去进行,而是时代内容。在新的诗歌形式还不成熟的前提下,不能随意丢弃作为典范的古典诗歌,诗歌的问题绝非如胡适等人鼓吹的,白话诗文是活的,古文是死的,似乎推倒古文,采用白话文的形式,诗歌及文学就面貌一新。新文学或新诗的出现是不应以消灭古典诗文为代价的,二者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可以两存。胡先骕由此断言,古典诗歌作为学习范本,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他说“现世代之文学尚未产出,旧式之名作亦有时不能尽厌吾人之望。”[0]
所以在与胡适的论战中,胡先骕着力指出,胡适等人攻击的清代旧体诗不是输在形式上,而是内在内容不够,这是时代所造就,非人力所为,或者说那是时代的缺陷,而非文体之过。他说:“以曾受西方教育,深知西方文化之内容者观之,终觉其诗理致不足,此时代使然。”[1]这里所谓的“理致”,不仅是时代精神和创作经验的问题,更主要的是现代学术发展所带来的理论深度及思考力。换言之,随着各种新学术的发展,新诗自然会结出成果,但它不是割裂历史,推倒过去的后果,而只能是新旧文化融会的结晶。在展望中国新诗的未来时,胡先骕无限期待地指出:
他日中国哲学、科学、政治、经济、社会、历史、艺术等学术逐渐发达,一方面新文化既已输入,一方面旧文化复加发扬,则实质日充,苟有一二大诗人出,以美好之工具修饰之,自不难为中国诗开一新纪元。宁须故步自封耶?然又不必以实质不充,遂并历代几经改善之工具而弃去之、破坏之也。[]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胡先骕及学衡派特别强调文学内容的“理致”及历史性,也即《学衡》杂志所宣扬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宗旨,从而把旧诗文纳入到了现代学科建设轨道中。简言之,文学的发展应在保持文体稳定性基础上,致力于内容的改造,创造出符合现代精神的新样式,这是在新文学视野下,以融通古今的方式进行的另一种文学改良思路。
总的来说,它是以西方学术体系为理论基础,对于传统进行现代性的思考和转换,但它不是“整理国故”者的“打鬼捉妖”,而是挖掘文化遗产的光辉一面,为其注入新的生命力,也即《学衡》宗旨中所说的“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而后来学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规。”在这一思路下,胡先骕主要做了三件事情:一是继续进行古诗文创作,但已有意识地融入了现代意识,以期在逐渐改造中为新诗开辟道路。我们可以注意到,胡先骕虽以旧体形式作诗,但内容及精神却是新的,如对海外各种新事物的描摹,异彩纷呈,为古诗开一新境界;将科学问题入诗,使枯燥的研究变得诗意盎然,钱锺书曾评价道:“堂宇恢弘。”[3]二是以现代学术眼光,运用西方理论对古诗文进行评析,这实质上是古代诗论的现代转型,属于文艺批评方向上的拓荒。他在《学衡》上发表的许多诗评文章,后来都成为了文艺理论方面的经典之作,如钱仲联等学者多引其论,极为推崇。三是对旧体诗的历史发展作了梳理,胡先骕在通观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基础上,着重白癜风治疗的医院北京看白癜风哪家医院最好